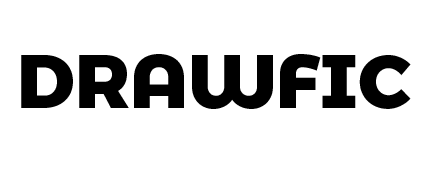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
作者帖子
-
15 10 月, 2022 9:06 上午 #1600
Akr
参与者翅鞘
腹中似有千百根针刺一般,尖锐的疼痛自喉管起蔓延到胃的底部,在忍者的脑中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叫他难以真正闭上眼睛,沉睡过去。
明知每天送来的食物中掺有药物,但眼前被困在不知是哪家势力的地牢中,为求更长远的自保,忍者还是会吃下能够维持自己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量。可送餐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意图,第二天的食物中夸张到人的鼻子都能嗅出来的药量直接掐灭了他的幻想。无关紧要的疼痛似乎只是副作用之一,药物真正的效用在食物被消化的半个星时后开始显现。
被麻绳束缚的双手双脚逐渐脱力,让忍者难以保持站姿,只能躺下。同时,眼前出现纷乱的幻觉,让他在原本视物的基础上看到了许多不该看的东西。甚至还有幻听和幻嗅,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叫喊和低语,什么东西传出的甜或腥味缠绕在他周围,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而裤裆之中的性器也会不自然地勃起,敏感到随意挪动两下被布料摩擦就会带来过于强烈的刺激,让他又羞又怒,却又无计可施。
更折磨的地方在于,下药的人只是下药,然后就把他晾在此处。由于狭窄的地牢中没有其他人,因此没过多久连他自己都卸下无用的礼义廉耻,跪到地上挺腰在床边磨蹭,并在放肆的哭喊和呻吟中射精。如此被药物折腾了好几天后,忍者的身体也逐渐产生耐性,能更快地恢复清醒。到了这一天,他飞快地从神思恍惚的状态中解脱,于是只能跪在地上喘息,感受着断续又漫长的腹痛。
忽然,他较之从前要迟钝许多地察觉到,有杂乱的脚步从远处传来,逐渐逼近。忍者强打精神,屈起身子把自己摆成一张弓的姿势。等到橙黄色的光从门底缝隙中穿来,来者停在门口时,他狠狠用牙咬住口腔内壁的一块肉,强逼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
随后一人推开地牢的大门,一名身着黑色羽织的男人提着一盏灯领着一个人走进来,席地坐下。那昏黄的光晃到忍者的眼睛上,在对方吹熄油灯之前,忍者瞧见他的肩头上有一面熟悉的绣样。
“久等了。”
那人将灯盏搁在地上,忍者嗅到劣质煤油燃烧后的焦臭,以及一丝微妙的血液腥气。似乎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刚从事过比较见不得人的活计,但在来这间地牢之前进行了简单的清洗。
在黑暗中忍者能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他不敢妄下定论。但十有八九,囚禁他的这伙人来自多玛本地一个名声显赫的家族。十数年前忍者也曾为他们效忠,可惜一场由帝国人主导的暗杀让它沦落为一支旁系亲眷当家的傀儡。前些时日他正是接下了一桩有关“来自多玛的叛徒”的任务才只身来到此地,不想线人提供的情报与实际情况有着极大偏差,忍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动手就从暗处被揪出来拿下。这次极为难堪的失手直接让他丧失自由,被蒙上眼睛关押在这里直到今日才终于等来审判。
对方也无法看清忍者的样貌,于是伸出手抚上他的脸颊。粗糙的掌心生着几颗厚实的老茧,从忍者的眼尾刮下去,在他嘴角停下。忍者认定这是一双拿刀的手,宽大的手掌将他的面颊拢住,合围起来。然后他们就这样保持着如此亲密又暧昧的姿势沉默十数秒,那人才重又开口:“还是点起灯,让我看看他。”
随行的人似乎是他的随从,听到他的话后左右走了两步翻找出什么东西才上前来用布条蒙住忍者的眼睛,然后又擦着火把灯点亮。橙黄的光从布条的缝隙中穿进忍者瞪得浑圆的眼睛,映出两个高大的人影。
“解开他脚上的绳子,再把他吊起来。”发令者又说到,他将一只手撑在盘起的膝头,歪着身子坐着。看着随从挑着眉一脸嫌恶地将忍者脚上的麻绳割开,然后像提起一条鱼似的把忍者提起来,挂在那条用作拷问的装饰横梁上。
“真瘦。”
坐在地上的人另一只手摩挲着腰间佩刀的刀把绳捆扎的绳结,眯眼看着那只猫魅被迫拉开身体,将自己最脆弱的腹部暴露在人的视野中,浑身紧绷到连尾巴都紧紧贴在下半身,作出攻击的姿态。这场特意谋划出来的重逢直到现在也依旧处于他的掌控之下,但即使是忍者的反应完全在情理之中,也依旧使他稍稍兴奋,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他抬起手摆了摆,随从会意,于是转过身抓住忍者额前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抬起,然后重重地掌掴下去。
这一巴掌够重,超出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范围。忍者未能躲闪开,半张脸连带被牙划破的口腔内侧在半秒后火辣辣地疼起来。然后接连十多个耳光密密地扇在他的脸上,扇得他的脑袋晃来晃去,眼睛里挤出泪水,脑子里嗡嗡响着蜂鸣。温热的鲜血从鼻腔里哗哗涌出,从他的嘴唇上淌下去。忍者缓了又缓,等了几秒没等到第十四个巴掌落下来的时候,他喘了口气,努着嘴朝面前的人啐出一口血沫子。
“再打。”人族垂着眼睛,望着滴落到地上的点点血迹,语气平静得与他眼神中的兴奋形成过于鲜明的对比。随从便将手捏成拳,在忍者的腹部比了个更适合出力的高度,然后一拳砸了过去。
这一拳让忍者闷哼出声。但并不是因为他耐受不了疼痛,而是满涨的腹部中填充着食物的残渣,膀胱中也积蓄着尿液。这样不留情面的殴打正在剥夺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且疼痛也让他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只能凭借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咬牙坚持而不至于泄力求饶。只是坚持了不到半刻钟,随从忽然更改了出手的方向而握住他的胸侧,曲起膝盖狠狠顶上来。
忍者哼叫一声,直接吐出一口带着胃液酸气的血水。随从撤手时,忍者蒙在黑布下的眼球都向上翻起,久久未能从疼痛的震撼中找回理智。
“好了。”地上那人深吸一口气,抬手把溅在他自己脸上的一滴血抹去后让随从抬起忍者的脸,“还能回话?”
忍者喘着气,微张的嘴上往下滴落着黏稠的血,没能及时作答。可那人却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你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多玛的猫,怎么会到黄金港来?”
“……”忍者未作任何反应,只是整个人往下坠着,两只手拉得笔直,手掌被绳索都束得充血发紫。
对方耐心等了一阵,接着补充:“还带着刀,躲在梁柱上头。又是只猫,险些没有发觉你……”他摸着下巴似乎在认真思考先前擒获忍者的场景,然后又仰头看向忍者被打得肿胀的脸:“是要杀什么人,报什么仇吗?”
忍者的手动了动。
暗杀一个多玛叛徒虽只是接下的任务,但其中却包含着过重的私心。他是多玛人,由于是少见的猫魅族,又是孤儿,忍者那靠偷窃维生和在挨打中度过的童年直到遇到那个人才迎来转机。武士见他被打得半死不活躺在郊外地上,主动将他带回家里医治,听闻他是因饥饿才盗窃,少爷心生怜意留他做自己的书童和护卫。
可如此安稳日子只过了几年,加雷马人便带着炮火来到多玛。因为明面上反对加雷马人的统治又在暗中支持革命军,武士一家死于暗杀。那时忍者并不在多玛,匆匆从外地赶回来时,只赶上一地异常惨烈的尸身。家主的首级悬挂在堂前门梁上,血从大门口一路流到后院的水井里,腥臭的气味浓郁到忍者险些跪地呕吐,但他仍坚持着翻看每一具尸体的脸,确认是否还有活着的人。
当他推开武士房门时,一个被削去了大半个脑袋的尸体朝下趴伏在武士的桌前,身上还穿着那件熟悉的和服。
被收留养育的恩情在惨案之后化为他昼夜难忘的血海深仇,为此他想方设法去往忍村学习,想要用同样的手段去报复每一个参与策划了暗杀武士一家的人。故而当他被打得头昏眼花,已经无力去思考那个对他喋喋不休的人的声音是多么熟悉时,他想到的是那人羽织上的绣纹。
是武士的家纹。
“是……”忍者咬牙,含糊的话语中仍夹杂着真切恨意,他努力抬起头,强行把自己已经剧痛的脸拉扯,“是你!你这,多玛的叛徒、帝国人的走狗!我一定,杀了你!”
忍者努力睁眼,试图从布条缝隙间看清那人的脸,看看到底是谁为了权势将武士一家谋杀。可他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色人影,那人纹丝不动,并不惧怕他狠戾的表情,甚至轻笑一声:“还有力气骂得这样凶,可见打得不够狠。”
“去叫人来。”坐在地上的新任家主,多玛豪族从前的长子武士将他腰间的刀抽出来一截,又按了回去,“我要罚他。”
在随从叫人来之前,武士难得有了一段和忍者独处的机会。灯火晃动,忍者的样子与从前似乎并没有太大分别,只是随着年岁增长五官变得明朗,身体也强健许多。不过与能够正面作战的职业相比,他还是太瘦了。
忍者粗重的呼吸一阵阵传进武士的耳朵,血从他者的嘴角往下滑落,划出一条蜿蜒曲折的红线,延伸进他深色的衣领。武士缓慢地咽下一口唾沫,由于过于用力,会厌挤压喉腔来带轻微的阻塞感。等随从带人进来时,他已经调整好脸上的表情:“将他的衣服扒了。”
忍者一动不动,似乎并不把这种对待当作一种凌辱,任由这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把他从梁上取下来,再将他的双手重新绑在身后。为了方便行动而格外单薄的衣服被轻松撕开,几个用来保护要害的护甲被随意扔在地上,忍者遍布疤痕的身躯被灯火照成橙黄一片,被迫全部展现在武士跟前。只见他紧咬牙关,腿上的肉紧绷到发颤,却不肯开口求饶。
于是,一个人伸手,按在忍者饱胀的腹部,像挑拣货物那样轻拍了拍。然后又分开他的双腿,将他半勃的性器握住撸了两把。
“将他的尿孔堵上。”武士又开了口,随从点头应下。他走上前,从不知什么地方摸出一根细长的棒针,看来早做好了准备。然后他抬手去握住忍者的阴茎,用拇指撸下包皮后又刻意去揉搓对方的龟头。忍者虽未出声,但马眼渗出的前液已暴露了他真实的感受。对方便借着这点液体的润滑,将那根棒针极缓慢地插进忍者的尿道中。从未被异物侵入过的尿道十分脆弱,一寸一寸地被棒针撑开,挤出一条笔直的通道。
由于时常受伤,忍者并不畏惧疼痛,令他紧张的是棒针的存在会阻碍他射精或者排尿。他闭了闭眼,决定先看这些人下一步的动作。武士没再发话,但这几个人已经领会他的意图,开始抚弄忍者的身体。
媚药在忍者身体里还有残余的药效,处于一个不会让他对疼痛的反应更加迟钝,却又会对这种不轻不重的抚摸更为敏感的尴尬状态。忍者并不是没有接触过这种下作的药物,但除去靠意志力来抵抗之外他没有学到任何能解决媚药——他认为是媚药——的办法。这几个人族对于在东方地区少见的猫魅的身体似乎很感兴趣,见他如此如此强撑,便像抚摸猫咪那样爱怜地抚摸他的身体。几双粗糙的手刻意从他被打到皲裂的嘴角和青紫的腹部上重重压过去,其余的部位也逃不过拍打和拧掐。不知是谁的一双手拽住他的尾巴强行盘在自己的腕上,故意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朝尾跟撸动。同时还有一个人掏出一把短刀,将他的大腿内侧划出一条长长的口子。
紧绷的皮肤被拉扯出叶状的伤口,黄色的脂肪和深红的肌肉被血液迅速浸染。拿刀的人十分欣赏这道疤痕,竟伸出手来在创口里面搅动,沾满忍者的血后并起两根手指,从忍者的会阴往下探触到他的菊穴,想要借血液的润滑挤进去。
“好紧,还是处子吧。”那人嗤笑,“恐怕很难插进去,你最好乖乖听话,把屁股放松些,否则要吃苦头。”
“滚开!”
“好凶的猫。”那人并不在意忍者的呵斥,反而愈发用力,手指头找寻到他菊穴的缝隙便往里插入,“等会操你的嘴前一定将你的下巴卸了。”
忍者能感觉到自己干涩的后穴被手指强行挤开,甚至能体察到自己的肠子是如何紧密吸住那人手指,被挤出一个怎样的形状,叫他恶心坏了。他吞了口带血的唾液,然后忽然偏头叼住正在抠挖他耳朵的一只手,狠狠咬了下去。可惜因他的视力被剥夺,所以他在下嘴在一个不太合适的位置。尖牙没有对藏在笼手下的皮肤带来任何伤害,反而给出对方一个掐住他脖子的时机。他细瘦的脖子被钳住,直接被阻断了呼吸。
忍者被遍布周身的疼痛刺激,用力往上顶起腰,想要吸进一口空气。可那只手还加大力气,甚至手指头都掐进忍者颈子上的皮肉里。在这短暂却又被无限拉长的时间中,忍者发胀的脑子已经没法儿再进行任何思考,只能依靠本能去挣扎求生。他的肺都一同疼痛起来,疼得他整个人都开始发颤,但所能做的挣扎不过是无力地蹬腿,然后将眼泪淌进布条里头。直到那只扼住他的喉咙的手忽然松开,他猛地喘上一口气,同时身下的手抓住时机,一口气把手指顶进他的穴里。
被强行撑开时,忍者凝滞在那个深呼吸的动作上。在这个一个瞬间,极为短暂的瞬间里他想到了死,只求能尽快解脱。可他忽然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于是缓了过来:
“我一定……杀了你们,杀了你们……”
无力的话引来放肆的嘲笑,站在边上的武士却一动不动,似乎并未被触动。武士只是再次摸了摸自己腰侧的刀柄,然后在地牢的床上坐下:“继续。”
他平静地看着忍者被强行拉开双腿,还沾着血的后穴被粗壮的性器强行撑大。深色的阴茎将猫魅的后穴挤开,连菊穴的褶皱都被抻平。在忍者发出叫喊的同时,另一个人捏住他的脸,用掌根击打过去将他的下巴打到脱臼,才放心把手指头伸进他的口腔中搅动。
由于下巴被卸下又被性器把口腔填满,忍者的叫声都不成样子,不知道他是难受还是舒服,总之他的屁股在操弄的幅度中晃得十分诱人。他像玩偶一样被随意摆弄,站在一旁的武士却没有丝毫参与其中的兴趣。他只是十分好奇,布条之下忍者会露出怎样的眼神,是愤怒还是痛苦,还是已经被媚药征服,变成性欲的奴隶?
但他暂时没有让人揭下那块布的想法,或许他还没有酝酿好与对方真正重逢时应该摆出的表情。他只是指挥并观赏着这场轮奸,看着忍者被男人的性器凌辱折磨并回忆着多年前那场改变他人生的暗杀。倘若不是家仆穿上他的衣服躲在房里,或许连他也会一起死在那场屠杀之中。
流亡多年的生活让武士性情大变,再也不是那个会对路边濒死的野狗都抱有同情的富家少爷。只是他无论沦落至怎样地步,又一步步借帝国人的手爬回高位掌握了能够复仇的权力,也依旧无法确定当年不在唯独不在家里的忍者,是否也是谋害他们的叛徒之一。
忍者的后穴被粗长的肉棒顶开,操他的人肆意摆动着腰部,将忍者一次次顶起。他的脸埋在一个人的下身,张大的嘴吞吐着腥臭的性器,不断往外推阻的软舌仿佛是在卖力舔舐柱身一般侍弄。大量分泌的唾液搀着血迹顺着他的嘴角流下,让忍者看上去好像沉溺在性交中的娼妇。
武士叫来的人在忍者身上发泄自己的兽欲,受害者的感受自然不会得到照拂。既无法说话也作不出有效挣扎,忍者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保持清醒。被捆在身后的手紧握成拳,指甲用力掐进掌心。但与后穴被抽插到撕裂的疼痛相比,与乳头被揉捏吮吸、阴茎和囊袋被把玩的屈辱相比这样的疼痛实在无法转移走他的注意力。自被生下来直至今日,忍者都不曾了解到性交对于受身者来说是这样一件折磨煎熬的事。尤其这并非合奸,而是彻头彻尾的凌虐,这些人将肉棒插进他的屁股和喉咙里,还要用他的尾巴和头发手淫,将腥臭的精液喷射在他的脸上喉咙里,强迫他吞下。那股令人作呕的恶心从喉管深处往上喷涌,却因为无法自控而无法呕出。
忍者发出的断续呜咽实在可怜,轮奸者中就有好心人被他打动,在他嘴里射过之后就帮他把下巴安了回去。毕竟他此时没有力气,不会再咬伤谁的老二。此时忍者的肛穴已经被内射过一次,浓稠的精液被紧致的穴道挤出。阴茎还直直挺着,涨成紫红色,棒针在挤压中被推出来半截,但被及时发现塞了回去。
“唔……我……”
“什么?”有人听到他的呓语,凑上前去,“喔,你想尿吗?还不行啊,大人还没有允许呢……”说着把自己二度勃起的阴茎塞进忍者嘴里。
忍者的舌头并不不像那些对猫魅族缺乏了解的人所说布满软刺,而是和普通人的舌头一般无二,湿滑又柔软。人的鸡巴垫在那条肉上面,被像是舔舐一般无力地推阻时,只会想要用力地像斜下方施力,狠狠用自己的龟头碾过去直顶脆弱的咽喉。
他的嘴和他被操开的屁股一样舒服,连忍者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此刻的颤抖似乎并不单是来自疼痛。勃起却被堵住的阴茎可怜地翘在腿间,随着他大腿的颤动而颤动。他温暖的、被精液射过一轮又一轮的肠子一阵阵地收缩,让轮奸者都对他的后穴赞不绝口,拍打着他的臀部继续顶弄。
忍者只知道自己好像又进入药物带来的幻觉里面,明明眼前被布蒙着,却依稀看见斑驳的色块,以他无法描述清楚的形状侵占着他的视野。嘴巴被操得麻木,先前有粘稠得像膏脂的精液涌进他的鼻腔,导致忍者直到现在还能闻到一股浓郁的精臭。下半身更是被玩得失去控制,陌生人的阴茎每一次顶入都会冲撞他涨满了水的膀胱,甚至能让他恍惚听到水液晃动的声音,憋尿的感觉让他几次险些出声求饶,好在吃着肉棒的嘴实在腾不出说话的空挡。
让忍者彻底崩溃的是最后一个使用他嘴的人,那人似乎已经射过两次,疲软的阴茎强行挤进来也不能完全硬挺。于是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提起,按在跨间直接在忍者口中撒起尿来。
“唔啊!不、唔……”滚烫又带着异味的尿液涌进忍者的口腔,忍者被冲刷得直接清醒过来。他疯狂地挣扎,扭动着身体,依旧无法阻止对方把他当作尿壶使用。
被迫饮下污浊的液体,食道都好像被灼烧一般,脸上身上都是溢出来的东西整个人散发着尿骚。忍者本并不害怕沾染污秽之物,毕竟在任务途中也不能时时保持清洁。可是,他早已被幻觉和轮奸折磨得神志不清,理智丧失,也无法保持镇定。于是他蜷缩起来,用头把自己身体顶起,然后不住呕吐。先前吃下的食物混合着胃液和秽物,以及被刮伤的口腔中流出的血一齐喷溅到地上。没有通风的地牢直接被浓重的异味填满,就造成这一切的几个人都退开两步:“真他妈恶心……”
这时,一直沉默的武士抬了抬手。他走过去,弯腰捏住那根棒针的顶端,缓缓将它从忍者的阴茎中抽了出来。即使灯火微弱,也依旧能看清忍者的性器已经涨成极不正常的颜色。甚至此时褪去了阻塞,忍者的阴茎却还是挺立着,什么都射不出来也尿不出来。
于是武士解下腰间的佩刀扔在地上,然后挽起袖子,俯下身去一只手掐住忍者沾着秽物的脖子,一只手捏成拳抬高,然后朝着对方的腹部狠砸下去。
“啊!啊——”忍者在这不留情面的殴击下短促地惨叫了两下,然后就被掐断了声音。他只能仰着头,被武士一拳一拳打到失禁,在疼痛和完全地脱力之中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敞着腿尿过后又抖着鸡巴射了精。
他所有的尊严和廉耻都在这短短两个钟内被武士剥去了,在窒息之中,武士的拳头似乎越来越慢,疼痛似乎也在离他远去。忍者松开了自己的手,同时也放弃了所有的挣扎。
忍者想要闭上眼睛,可是他知道自己一闭眼就会看见多年前惨死在家中的恩人全家。倘若他不活下去,大概再没有人会为他们报仇。
但是,要怎么活呢。打在他身上的拳头似乎没有准备给他留活路,从身体的反馈来看,说不定肋骨都被打断,内脏都破裂了。且他在武士的钳制下只能艰难吸进一点空气进肺里,再不被放开或许真的会被活活掐死。
武士知道就算忍者想要服软,他不松手忍者也无计可施。虽他的拳头很干脆,可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忍者表露出怎样的态度。他只是挥拳,打得自己手臂都发酸,然后抬头想看一眼忍者的脸时,发现那根束在忍者脸上的布条松垮了。那双充血而发红的眼睛,死死地与他对视。
他松开手一把将忍者推开,踉跄起身一脚踢翻地上的油灯。灯火熄灭,地牢回到黑暗之中。武士的随从不知他又发了什么魔障,都静默立在那儿不敢说话。只听见一片寂然之中传出粗重的喘息,以及:
“你……变了,好多。”忍者的嗓子已经被掐坏了,沙哑到不仔细听根本无法分辨那是呻吟还是成形的句子,“我,险些没,没能认出你……”
本以为武士已经遇害,这么多年来只能在梦中和故人相见。可每每想起那张脸时,总又会联想到那个被削去头颅的尸身。那样善良的人,怎么会迎来这种结局呢?
武士落荒而逃后忍者又被关在了地牢,泡在污物之中过了不知道多久,他才缓慢地爬起来,挪动到门前拨弄门锁。发现门上着锁后他又撑着墙挪到床边躺下,然后闭上眼睡了过去。
在知道武士还活着之后他并不高兴,反而有那么一瞬间迷茫于自己这么多年的挣扎和努力是否有用。武士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自己面前,是否说明他已经和当年的暗杀者合为一流……忍者实在不清楚,自己要怎么去接受一个已经成为帝国人走狗的武士。
他沉睡过去,在梦中再一次被拉回多年前那场血案的现场。他总希望能在梦中窥见谋害者的脸好寻仇,或者再看一看武士,以免自己忘了珍重之人的模样。可这一次他变得迷茫,站在一地尸身之间,竟不知该走向何方。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忍者都没能再见到武士,其实能从那样重的伤势中醒来已经算得上奇迹了。第二天有人来收尸时见他睁眼躺在床上还吓了一跳,很快给他送来治愈的药物和老一样的吃食。从身体的恢复速度来看,忍者发觉药物和食物中肯定有一样有问题,否则自己必不能如此快地下地行走,甚至不像往日受伤那样半夜被痛醒。
不仅如此,他发现自己的感知能力也变得迟缓,狠狠往墙上撞去时只听到咚的响声,过一会儿才会感到疼痛。而幻觉仍在间或地出现,甚至愈发严重。等到某一天他才后知后觉,饭菜中搀杂的药物或许并非媚药,而是某种能破坏人神经的毒物。
忍者的猜想在接下来的试验中得到验证。拒绝进食后的第二天,从指尖到尾巴的骨骼都仿佛被千万只蚂蚁啃噬般刺痛。为缓解疼痛而把身体摔到墙上而不起作用时,他很快变得焦虑,不住锤击墙面然后走屋内打转行走。忍者特意训练出的冷静被药物摧垮,他听见耳中传来自己过快的心跳,于是害怕得大声叫喊。又控制不住地流泪流涕,感官在过冷和过热之间交替。
明知道是药物成瘾带来的作用,忍者的意志力却已不足以坚持到再次拒绝进食。新的食物被送来时,他发疯般扑上去用手抓着食物囫囵塞进嘴中,被一脚蹬开还跪到地上去拾捡着吞下。
清醒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之中,是几乎每个想要戒毒的人都会经历的阶段。在两种痛苦之中交替,忍者的形容很快变得枯槁。甚至到后来,送饭的人只是送来普通饭菜,而采用注射的方式给他喂毒他都不再挣扎。
“只是……”
长久没有听到忍者讲话,随从注药的手都抖了一下。他抬头看向忍者,那猫魅低垂着头,睁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空洞地注视着地面。
“什么?”
“只是……”忍者将头彻底低下去,掩盖住自己脸上的神色。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在毒物的作用下变得兴奋,失去神智而被低等的兽欲支配,成为一个只想要交配和乱尿的牲畜。但他还是坚持把话说了下去:“我还是,想要,再见他一面。”
随从没有及时给出答复,他不敢作出担保。毕竟武士那日离开地牢后,一开始看着还好,忽然把参与轮奸忍者的其中一个人叫到他房里去。很快那人的惨叫传出来,然后捂着眼睛跑出房里。几个人伸着脖子往里头看时,竟发现武士捏着一柄木勺,是用勺子直接把那人的眼球从脸上舀了出来。此后武士又迅速恢复正常,好像从没做过这事一样撑着假笑去那人家中送礼安抚,把那人的妻子吓得瑟瑟发抖。
他沉默着退出去,转身时被吓了一跳。武士正站在门口,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斜眼瞧着牢里靠墙坐着的忍者。
“久等。”
随从被叫走后,武士坐到忍者跟前,又这样客客气气地打了声招呼。忍者深吸了一口气,抬起自己细瘦的胳膊擦了一把脸,才抬起头:“那个‘与帝国有紧密联系的多玛叛徒’是你?”
“是。”
“给我提供情报的人也是你?”
“是。”
“好狠。”忍者笑了一声,似乎处在疯魔的前奏。不过他说完这句后就重归沉默,武士也不主动与他交流,二人在死寂中对峙。过了一会儿,忍者深吸一口气然后坐起,揪着衣服想把自己的双手和脖子擦拭干净。他的双手不住发颤,也把控不好力道,不仅没有把那些脏污擦掉,反而还在自己身上划拉出好几道红痕。
准备工作虽然不够到位,但是药物已经开始发生作用。忍者颓然放下手中衣物,跪行到武士跟前抱住他的腿,把脸贴在对方膝盖上然后支起身子。一路向上,他将自己带着臭气的身体挤进武士双腿之间,然后把脸埋在对方的胯部。脑子虽然还很昏沉,忍者却还能作出武士所穿的柔软衣料价值不菲,大概如今混得不错的判断。不过更占据支配权的,是他被毒物强制引发的兴奋中一同升起的肉欲。
“操我,操我……”忍者用力掐住武士的羽织向下拉扯,然后声音陡然提高“操我,你不是就想我变成这样吗!”
武士一动不动,手还搭在他的佩刀上。忍者得不到回应却变得焦躁,直接咬住面前的衣物开始撕扯。他此刻脑子里只有和武士做爱这一件事,不仅阴茎勃起,甚至后头都湿了,只等着武士插进来。
被本能牵着走时,忍者终于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毕竟他总是想到要为武士全家报仇,因而无法面对这样的武士。这几天他在清醒时想过许多种可能,譬如武士是遭到胁迫,或是有他自己的原因。
“告诉我为什么!”忍者大喊起来,“我要知道原因,你告诉我,否则我……”
话说到一半,他自己打断了自己。他已经爬到武士腿上坐下,一口咬住对方的肩膀。武士的手从他背后抬起来,似乎想抚摸他,可转手揪住忍者的头发,把他一把拉开。
从家中逃出去后,武士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的日子。他生怕被多玛城内的暗哨发现,连身上家仆的衣服都不敢再穿,去偷了别人的衣服套上。四处游荡寻找能落脚的地方时,由于他身上沾满脏污,且拿不出能证明身份的东西,所以甚至没有哪家店敢在这种紧张时期收他做工。
他只好更名改姓离开多玛,过上漂泊流浪的日子。此后他给人做过学徒,为人拉过鸟车、做过侍从,甚至被收作娈童玩弄。他苟活多年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靠着什么东西活下来,有一日他看着地图想着回到多玛的路,突然记起那一日忍者是被委派出去做事而不在家中的。于是在重新接触到帝国人,并摸到权力的边缘之后武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听忍者的消息。得知他成为忍者,并在黄金港一带从事暗杀活动时,武士便叫人与他牵线,诱骗他来到自己临时落脚的府邸。
忍者在他身上磨蹭,力度上没有分寸,却还是十分亲昵。他已经自己脱掉了裤子,用手撸动着自己的性器在武士腿上挪动,寻找着那一天被轮奸时的快感。见对方半晌没有动作,他伸手去握住武士搭在佩刀上的手:“为什么不理会我,你究竟要做什么……”
武士翻手握住忍者发烫的手腕:“不要碰我的刀。”
忍者没有应答,他的脑子暂时还处理不了武士的话。只知道武士似乎是拒绝了他的示好,于是他激动得流泪,愤怒地撕扯武士的衣服,将自己脏兮兮的脸贴在对方的胸膛上。听到熟悉的心跳,他似乎变得平静。可他不知道,自武士踏进这间地牢的那一刻起已经预想过无数次拔刀,将他砍杀。
只是忍者忽然抬头,亲吻武士的胸口、锁骨和喉结。武士又想起曾经与忍者一起生活时,这个虽年长自己一两岁可瘦弱得和自己弟弟差不多大的猫跟在自己身后的样子。
“来日方长。”武士的手往上移,他摩挲着忍者手臂上的针孔。忍者的泪水滴到他的手背上,好像一声叹息:“我会把你做成最好的刀鞘。”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