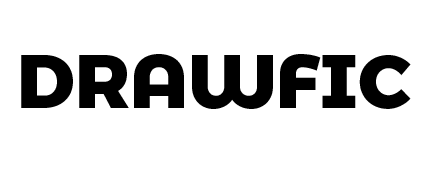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
作者帖子
-
19 3 月, 2023 6:50 上午 #2250
Akr
参与者致亚当。
学者亲吻了他的兄弟召唤的腹部,那里有一条长的创口——从召唤腰部的左侧到右侧劈开的深红色裂谷,翻白的皮肉与黄色脂肪撕裂如同棉絮。粉色的肠外溢出来,像盘卧的蛇,一齐被血液浸染。
浓郁的血液腥气占据学者的鼻腔,随着他的呼吸灌进他的肺部与大脑。铁锈的甜味通过他双唇之间的缝隙淌进他的嘴里,在他舌尖晕开。召唤的血就这样进入他的身体里,成为发动某种诅咒的媒介。这种诅咒催使他朝召唤伸手,将五指插进召唤破损的皮肤、柔软的内脏之间。
与他在学习时解剖尸体,带着薄薄的橡胶手套捧起被切割的脏器时完全不同,召唤的身体是温暖的。当他的手进入召唤的身体里时,仍跳动的血管、仍蠕动的大肠与仍流淌着的血液都在向他传递温度。他并非冰冷的,而是滚烫的。
他并非不可逾越的,而是脆弱的。
学者将他染成粘稠红色的手抚上召唤的脸,他的拇指从召唤因剧烈的疼痛而不住发颤的嘴唇上抚过。与曾经每一次面对召唤时不同,他从这张与自己长相相差无二的脸上头一次见到恐惧,就好像在看镜子里的他自己。
“你从神坛跌落了。”他的手把召唤的手按住,他们的指尖一同触碰到那本魔导书用金属和宝石雕琢的坚硬外壳。他的宣判平静又低沉的落在召唤耳边,像冰锥,尖利地砸了下去。召唤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
距离他腹部受伤已经过了大概两个星时,血液从他身上的每一处创口外流,令他在疼痛之余还被一种彻骨的寒意包裹。他认为死亡是冰冷的,死亡正从他的指尖开始将他吞噬,一起将他吞吃的还有他的弟弟。学者并没有像曾经每一次所做的那样,克制着心底的憎恶接纳受伤的他为他治疗。当他在学者房间里那张熟悉的床上躺下,学者亦如往常搬来药箱,并抬手用使用魔法为他止血时,学者的动作忽然停滞了。
某种威胁像毒蛇一样舔舐了他的脖颈,他被这种毛骨悚然的寒意惊吓,急忙睁开眼睛。学者正坐在他的身边,用手抚摸他被利器切割翻开的伤口边缘。这种刺激加重了他的疼痛,使他本麻木了的身体重新振作了一阵,立即发起颤来。他难得感到畏惧,但他首先没有畏惧学者,而是像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畏惧伤口感染、内脏破裂、失血过多以及后遗症。直到学者忽然亲吻了他的腹部,吮吸了他的血液,他这才开始害怕他真正该害怕的:“……你应该治好我。”
召唤在开口的那一刻后悔,颤抖的声音暴露出他的恐惧。他一向自认目光毒辣,尤其对于学者,与他一同长大的弟弟从来都是擅长做低伏小,纵使憎恶他对自己的控制,也不敢拒绝他的任何请求。他们从同一个子宫孕育,连接同一条胎盘,相同的血液在他们相同的血管中穿过拥有相同心跳的心脏,却在性格上大相径庭。血缘和强权正是召唤驾驭学者的工具,而学者亦是他掩埋罪行、四处享乐最好的工具。他时常并不把学者视作自己的兄弟,甚至不视他为一个完整的人。他肆意伤害学者的身体,甚至强迫对方脱下衣服安抚他无处发泄的性欲。
但是驾驭牲畜是无趣的,召唤尝试刺激学者作为一个人反抗他。他得知在某一家花店,有个女孩会在学者固定去买花的日子为学者留下最新鲜的一束,百合、桔梗、向日葵……在学者下一次拜访花店前,召唤在他胸口别上一朵妮美娅百合。
“她失踪了!”学者难得是激动地推开门,冲进屋内,“她失踪了,是不是你!”
召唤笑起来:“我们不是兄弟吗?”他嘴角的弧度随着他的话语变大,于是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格外虚假,“作为兄弟,你为什么要把我想得这么糟糕?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嗯,会为了……你?谋杀一个完全无辜的女孩?”
召唤是会把自己的娱乐凌驾在任何人的痛苦之上的,他并不精心策划犯罪,而是肆意散播自己的恶意。这反而使学者陷入深深的对自己的怀疑之中:在召唤如此轻贱他的情况下,为什么召唤会为了他杀人?而作为召唤的弟弟,他是否也该为了这些罪行担责?
学者的懦弱使他再一次的沉默了。召唤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越发肆无忌惮。自多年分别而重逢后,召唤时常在受伤后寻找学者。于他而言,学者的家不仅是他疗伤的诊所,更是他取乐的圣地。这位对他满怀不满的弟弟每次都会服从他的话语,克服极大地不情愿而举起魔导典,将自己的以太输送进他的身体,为他治疗。召唤每次来学者的家,学者所精心打理的一切都会被打乱,尤其是帮他治伤的床。就好像学者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生活总是会被召唤弄成一地狼藉。而召唤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欣赏学者的憎恶与顺服,这就是他喜爱的东西。
但这次情况发生了完全地改变,或许是一切都必须划上一个句号了。明明还是那双眼睛,学者的目光却令他陌生。他的手被学者的手以及他已经凝固的血液包裹,却丝毫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当学者俯身与他贴近,鼻尖悬在他的面上一指的距离,带来极强的压迫感时,召唤忽然大笑起来起来,有些癫狂。他的声音还因受伤而虚弱,因此断断续续:
“我觉得,你,终于变得,有趣起来了。”
学者的手插进他的脏器更深处,搅动一汪血水。黏稠的液体在他指尖划过,引导着他粗糙的指腹在湿滑的肠子表面摩梭。他捏住蛇的尾巴,将猎物完全桎梏在自己掌心,但这完全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他必须如召唤凌驾在他身上那样凌驾召唤,不仅是肉体,更有魂灵。于是他的手从召唤的脏器之间穿梭过去,他没能抚摸到召唤的脊柱,这条与肌肉粘合在一起的坚硬骨骼,支撑着召唤作为一个人而直立。油布一样的肠粘膜像海藻一样把他缠绕,阻碍他的手继续前进。
他试图将手往上移,他想要握住召唤的肋骨,乃至被鸟笼一样的肋骨围绕起来的胃囊、肝脏、肺叶和心。但这个伤口无论如何已经不能被拉扯得再大了,他的审判必须在召唤活着时进行。
“你曾猥亵过我,数次,数之不清。”学者把手缓慢地抽了出来,他瞧见召唤额头上的汗珠如泪水般滑落,“作为报复,我也将进入你的身体。”
学者用一把剪刀剪开召唤的衣服,它们被血液粘连在召唤的皮肉上,怎么都撕扯不开。且剪切是一种更为彻底的破坏,代表他剥夺了召唤身上的遮蔽,叫召唤赤条条地袒露。在他将召唤一步步剥干净的过程中,遍布对方身体的大小创口一条条呈现在他眼前。他曾为召唤治疗时总是竭尽全力,不会留下一寸疤痕,可今天他只是用一点法术吊住召唤的命,不至于叫他立即衰竭,又保留了全部的疼痛。
他像是按摩一样揉搓着召唤的双腿和双臂,五指在那光滑的皮肤上留下一片红色。学者的眼睛在这片红色的刺激下收缩,呼吸也变得急促。召唤的身体激发了一种阴暗的欲求,令学者心跳加快,性器官也勃起。
学者深知,这是他掌握了召唤的生死的奖励。他用带血的手握住召唤的性器,在卷曲的阴毛中,沉甸甸的囊袋被他捧在手心,缓慢揉搓。脆弱的睾丸在他的手掌根部不受控制的滑动,直到他合起手掌把它们固定:“让它坏死很容易,人类的性器官总是尤为脆弱的。”
随后他短暂地沉默,短暂地施压。召唤的目光从他自己高高竖立的阴茎一侧穿过去,他想看清学者此时的表情。但学者低着头,抬手握住他性器的柱身,上下撸动。这双巧手能精准地把人切割,寻找到埋藏在身体最隐秘角落的病灶进行手术,也能精准地把他掌握。温暖的掌心把他的肉茎包裹,粗糙的指腹在膨胀的血管上摩梭。修剪整齐的指甲掐住他敏感的龟头,令他在清晰地疼痛和迟缓的快感中泌出前液。
“你还能勃起,说明伤得不够严重。”学者的语气平静,他的评价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像机械人偶念读诊断报告,“也可能我输送的以太过多,给了你你不该有的生命活力。”
他的片刻思索中,召唤已经勃起得更加厉害,透明的腺液把学者的手指都打湿:“我,觉得,都不是。”
“是你我血脉相连,我在勃起,所以你也被诱发了性欲。”学者低头含住了召唤的性器。他的口腔像潮湿的洞穴,柔软的舌头缠缚上去。
召唤曾很喜爱学者的口活,细腻可爱,但此刻这种细腻成为催发他伤痛的触媒。学者没再和从前那样,巧妙地把牙齿包裹在嘴唇后面,而是令他尖利的齿间在召唤的柱身上刮过。召唤的身体便随他每一次俯身而发抖,卑微的呻吟也漏出沙哑的嗓子。他的舌头尝试钻入细窄的马眼,舔舐吮吸出更多的咸腥黏液,搅合进他的唾液之中,被一并吞下。随后将召唤的龟头搁进他的臼齿之间,用崎岖的接合面摩擦脆弱的蕈头。
这种连绵的疼痛与快感相互掺杂,汇成一条汹涌的河流从召唤的下半身冲向他的大脑。召唤仰起头,发出短促的呼喊。尽管天性令他享受这场凌虐,但本能又令他萌生逃跑的意图。他在此刻忽然理解学者,置身于这种无论是从生理还是精神上都无法逃脱的境地会是怎样地纠结绝望。学者已经完全脱离他的控制,因此召唤无法预料在单纯地羞辱过后,学者是否会杀了他。
他在学者的眼睛中窥不见杀意,但人想要碾死一只蚂蚁是不需要杀意的。
“你没有选择权。”学者吐出口中的东西,“现在,你必须把腿张开。”
召唤的双腿被迫张开了。学者分开他的臀肉,触摸他的后穴。这些深色的褶皱因紧张而收缩,不肯对学者敞开更多。于是学者用他带着血的粘滑的手指强行从中央挤入,先是破开一个细小的缝隙,随后完全深入。里面是干涸的山谷,未曾有人如此强硬地入侵。如果是医学上的指检也会有消毒和润滑,但此时只有血液。召唤被这撕裂般的疼痛引发高昂的惨叫,但学者却将他的手指插进更深的地方。
召唤的叫声在疼痛到达某个高点时失去声响,正是学者在不带其他润滑的情况下,把他的第二根手指并进去并分离,把他的后穴成一个洞口的一瞬间。
学者心想,这样程度的前戏完全不足让他轻松进入。且作为医者,他本该追求更洁净的环境,但他此时和召唤一起泡在血污中,他雪白的床单都一起被染成肮脏的深红,他却觉得喜悦而不可自拔。学者愿意在这样的情境与召唤沉沦,于是他脱下裤子,掏出他的性器。他的阴茎挤进他亲手劈开的这个洞口,硬生生碾了进去。
他伟大的征服从这一刻开始,如车轮滚滚。他将征服召唤的全部,令召唤的肉身与魂魄都拜服在他身下。他克服阴茎的疼痛将召唤拥挤的穴肉层层破开,在召唤因疼痛而紧蹙的眉毛中心,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成就感。
学者在召唤身前直立身体,他像一尊崇高的石像把召唤压迫。当他掌握权力,掌握召唤的生死,这种快感甚至超脱他身体所享受的愉悦,令他无比畅快。在他身下的并非他的兄长亦不是他的仇敌,而是他能随心所欲把控的玩偶。即使是因强奸了生涩的处子穴而疼痛,他依旧要反复进入召唤的身体,以抽插这种最原始的交配形式宣示地位。
“我的兄长,你太过脆弱。”
学者轻轻抚摸召唤的腹部,魔法从他的指尖流淌,修复着召唤暴露在空气中的脏腑与被切割断裂的神经。这种恩赐令召唤好受了一丝,仅这一丝的好处就让他甚至露出感激的目光。但点到为止,召唤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更走近死亡的边缘。学者便握住他的肠子,往下撸动,他尝试找到大肠,自己阴茎进入的位置。召唤成了他泄欲的工具,也成了一个肉做的阴茎套子。学者无论怎样进入他的肠子,他都无法作出更多的反抗。
召唤已经几乎要陷入失血导致的休克,又被疼痛一次次呼唤到清醒。而在反复退出又进入后,学者发觉快感已经越过疼痛,令他萌生出射精的欲望。权力的颠倒本身就给他带来足够的快感,一步步把他催化成一个他陌生的形象。当学者坐在召唤的胯间,用手抬起召唤受伤的双腿,不顾他腹部的创口而施放兽欲时,他被塑造成新的“召唤”。
这一刻,他并非是从他和召唤共同的母亲身体里被孕育的,而是从“召唤”中诞生。
学者并没有选择在召唤的后穴中射精,一切才刚刚开始。人犯下重罪,他的骨肉至亲首先惩罚他。学者将自己当作刑具,他的每一次进入都是鞭笞。召唤因疼痛而五官扭曲,发出畜类的呻吟,高昂地穿破屋顶,穿破学者的耳膜。他的惨状鼓励着学者,让他不被限制在单一的刑罚上。
他的目光被召唤的腹部吸引,这个狰狞的创口正像是鲜艳的禁果,今日召唤所承受与学者所享有的一切都来自禁果的诱惑。于是他把自己从召唤的身下抽出,这个稚嫩的后穴已经承受足够多,被撕裂出细小的伤口。血液掺和着血液,汇成一股浊流,从他肿胀的褶皱上流淌下去。如果是从前的学者,必定会强忍着恶心为他清理伤口,治疗伤痛。但这次抽离后,学者不过是随手拿起召唤的衣物擦拭了双手。他放开召唤的腿,他擅长使用法术战斗的哥哥并没有一双强健的腿,腿内侧的肌肉柔软得像是棉花,被他轻易掐出几条深深的指印。
这几条指印像是岩壁上的刻痕,它们提醒了学者,应当把召唤的罪烙在他身上,一条条宣读下去。
但太多了,他无从记起,于是他只好套上一个足够宽泛的罪名:“你对我不够恭敬。”
这句话代表他接下来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报复,强者不会怨恨弱者,掌权者不会怨恨被他统治的人,神也不会怨恨无能的凡人。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拥有这个权力,即使召唤完全无辜。
学者把他的性器从召唤腹部的创口中插了进去,他深色的阴茎上还挂着污秽,但他并不在乎这是否会诱发伤口感染。他恩赐以太为召唤吊着命,让召唤无法昏迷好让召唤感受他的暴行。召唤的内脏比他肮脏的灵魂要柔软太多,它们将学者的阴茎缠绕起来,像盘旋的蛇。尽管学者并未因此感受到更强于在召唤后穴中的快感,但他依旧无比愉悦。
他在此时才开始有了人类真正交配时会做的举动——他俯身把他的兄弟亲吻,以绝对强硬的姿态啃咬对方冰凉的嘴唇。学者的舌尖舔舐到他先前用手抹上去的血迹,它们干涸成薄薄的痂皮,瞬间被他的唾液融化。随后,他带着这苦涩的唾液深入,撑开召唤紧咬而发颤的牙,挤进口腔内部。召唤的牙齿在他的舌面上打颤,因为他实在太疼了。他几乎浑身都疼,但只有来自腹部的疼痛无法忽视。时间在他的眼前被无限放慢,每一秒都煎熬无比,因这疼痛是他无法回避、无法抗拒的肉身之苦,且随着学者用鸡巴强奸它的动作而愈演愈烈。
人的大脑会在身体遭受无法承受的疼痛时切断神经的连接以作自我保护,但他却怎么都无法陷入昏迷。他此刻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沉入一场长久的安眠,把他与疼痛完全隔绝。作为学者的孪生兄弟,召唤已经深知学者不再会为他治疗,只是一切都超出他的掌控,他无法判断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学者的亲吻结束后,他的嘴唇熟练地下移。他一寸寸往下啃咬召唤的皮肤,从下颌到喉结,再到锁骨和乳头。他从一条条疤痕上掠过,总共三条,还有擦伤、淤青。它们像是召唤身体上的破洞,使他变得窘迫。
他的亲吻几乎不带一丝亲密的意味,但他的阴茎却是在认真地强奸召唤的肚子。粗大的阴茎顶住油布似的肠粘膜,在肠子的外衣上反复摩擦,龟头在肠子的每一个回转处碾压,似乎在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G点。召唤破碎的叫喊被视作情欲的呻吟,与被污染的血液一起打湿了学者的全身。学者做得十分尽兴,鼻梁上铺着一层汗珠,他的动作越发加快,几乎要顶穿召唤的身躯。
“啊,啊!放过,放过我,唔啊!”
学者置若罔闻,他把精液泼洒进召唤的身体,然后重新直起身子,想要好好端详他的战利品。浊白的精液像一缕丝线汇进黑红的血液,在召唤大肠蜿蜒出的一个窝那里形成一滩水洼。学者对此番情形十分满意,然而当他抬起头,他看见召唤流着泪的眼睛将他死死盯住。
他熟悉这个眼神,当这双充满了恐惧的眼睛出现在一张与他长相相差无二的脸上时,学者忽然看见了自己。而在召唤的眼睛中,他又看见了自己与曾经的召唤没有任何分别的脸。
一种冰冷的恐惧爬上他的脊背,令他浑身僵硬。他忽然记起来自己应该是仇恨召唤的,可他的行为却分明不出自仇恨,而是一种玩弄猎物的轻浮心态。而无论他曾经多么憎恶召唤,他此刻的行径与召唤又有什么区别。
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就像你道貌岸然了一辈子,临终才在镜子里发现自己丑恶不堪,令人作呕。
“你……我……”他抬起自己沾满了血的手。血液凝固在他的掌纹之间,向一张网把他沉重的罩住。他颓然地躬起背,低下头,痛苦地揪住自己的头发。
因他们的身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所以他们共享安乐,共享罪责。当他们一同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曾经历的一切以及今日的选择都已经写定。一切都像是一个轮回,就像蛇因饥饿吞下自己的尾巴。而学者无法窥见更未来会发生的所有事,但没有哪一件能比他此刻意识到,他的灵魂真真切切地与召唤相连要更为可怕。
除非某一方死去,否则他们将永远捆绑,永不分割。
学者在他的指缝间瞧见召唤剧烈起伏的胸膛,他的呼吸也随之一起加快了。学者知道,自己显露出如此丑态的伊始正是他意识到能掌握召唤生死的一瞬间。如果召唤没有在受伤后出现在学者面前,没有把他的弟弟当做玩具随意欺辱,更没有与他共同出生,那学者本该拥有一个完整的灵魂,他本该无罪。
学者看向药箱里的手术剪、解剖刀,看向里面预先调配好的麻醉药。他看向罩着玻璃外壳的台灯,看向搁在床头柜上的魔导典。
他看向召唤的喉管,最后看向自己的双手。
血液铺散在他纯白的床单上,鲜红刺目。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