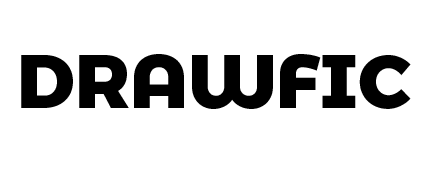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
作者帖子
-
18 7 月, 2023 12:12 下午 #2563
DickDiver
参与者忘忧骑士亭还是老样子,木质招牌上落满了雪。
室内温暖得多,满地都是湿漉漉的脚印,偶尔会从别人身上闻到毛皮很久不洗的油膻,混着陆行鸟的臭味。
吟游诗人抱着杯子坐在角落,竖琴搁在墙边,脑袋一点一点的,就要睡着了。
“喂。”
半星时前才认识的新朋友叩叩桌面,诗人的耳朵竖起来,往声音的方向转了转,眼睛还眯着没睁开。
“你听见他们说的没?”那人悄悄指了指旁边那桌,“天钢机工房来了一个新学徒,是个兔人。”
诗人以为自己睡晕了:“什么兔人,蛮族?”
“不知道,好像是密林里来的,他们那个种族叫维什么,全都是兔子。那人很白,长得相当漂亮。”
诗人把眼皮撩起来一边,狐疑地瞅着对方。
“你见过了?”
“远远看了一眼。”
“我也去。”诗人说。
说干就干,他把酒钱和小费压在杯子底下,背上琴,他的新酒友也跟了上来,两个醉汉一起溜达到天钢机工房,从门外伸长了脖子往里瞅。机工房对外开放,不过他俩干的不是正事,多少有点心虚。
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见传说中的新人机工,他穿得朴素,袖子卷过手肘,露出白得晃眼的小臂。他有一对长而机警的兔耳,随着动作摇摇晃晃,模样的确称得上是美人。
兔耳朵机工跟在前辈的身边,两人对着一尊机器人指指点点,他不时点头,从兜里掏出小本子唰唰记了点什么,抿着嘴,神情很认真。不远处,两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正对着他品头论足。
“原来是男人啊。”
“男人怎么啦,你不是说你都行吗?”
诗人没接话,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男的?男的更好了!
“看够了吗?是时候跟我去玩一下了吧,让我看看你这百人斩是不是浪得虚名……喂,怎么又不说话?”
一只手在眼前晃了晃。
“这个人,估计就算是你也拿不下。外地佬不太会说通用语,是个哑巴美人,你就算给他唱歌,也是对牛弹琴。”
诗人啧了一声:“你等着看吧。”
对方怂恿他上去搭讪,他却摆摆手说今天不行。“喝太多了,起不来的。”
“你还真想睡他!那我呢?”
诗人的确已经醉得懵了,蛇一般的竖瞳都扩圆了些,迟钝地呵呵一笑。
阿——嚏!
年轻的机工士学徒打了个喷嚏,耳朵抖了抖。
第二天,诗人酒醒了以后难得还记得这件事,兴致很高,吃了饭就去天钢机工房外面蹲着。他背着琴,衣服像冒险者一样旧,有许多花哨的装饰,一看就是吟游诗人的模样,说话很风趣,不一会儿就和其他机工士聊上了。
可惜他们也不太了解这个新来的,只知道这家伙来伊修加德就是为了学习操控机械和使用火枪。
“机工房正缺人,伊修加德现在开放不少,就算是没见过的种族也招进来了。不过那家伙也真是大心脏,如果是我的话,被盯着看两天就受不了了。”
他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因为对艾欧泽亚文字不熟悉,每天会自己对着书研究到很晚,保安熬不过他,这一阵子都是干脆睡一觉再来锁门。
这么说来,只要留得够晚就没人打扰,还有这种好事。诗人出去转悠了一天,等到晚上,所有人都走了,大摇大摆走进机工房。
在伊修加德的娱乐活动不多,人们休息得很早,机工习惯了深夜一个人待着,突然,他的耳朵竖起来,循着脚步声望过去,看见背琴的猫魅族,露出讶异的表情。
诗人也装作惊讶:“我看见大门掩着,没想到里面有人。我丢了钱,没钱住旅馆,正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将就一晚上。”
“这里晚上还是要锁门。”机工说。
“你就让我在这儿悄悄待一会儿,想想今晚该怎么办吧。求你了。”
“唔,好吧。”
图纸长长地铺开,机工跪在地上写写画画,诗人走过来,蹲在他旁边,猫尾巴扫来扫去,蹭了一下他的脚踝,痒痒的。机工转过头,发现诗人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你的相貌很特别。”诗人比划着说。
他习惯性地用了比喻,甚至还押韵了,言语很优美。
机工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话太快,我没听懂,你说我的嘴巴像什么?”
“……”
“我的意思是,你很美。”
“很多人这么说。”机工点点头。他的语调平淡,坦坦荡荡,好像也没有自夸的意思。
他操起扳手,开始拧螺丝,如此正直而不解风情,让调情的话都无从说起,诗人沉默一会儿,把行囊都放在脚边,从包里掏出酒瓶来,自己喝了一口,又用酒瓶子底戳戳他:“喏。你会不会喝?”
天气寒冷,人走了以后锅炉也不烧了,机工房里温度逐渐降低。
机工点点头,灌了一口酒之后,手脚开始回暖。酒瓶搁在两人中间,不知不觉,就这样一人一口把瓶子喝空了。
“你酒量还不错。”
“唔。”
其实这是机工在伊修加德第一次喝酒,不同于蛋奶酒这种饮料,而是真正的烈酒,为了尽快祛寒,喝得太急了,想站起来拿东西的时候竟然一阵发晕,又坐回了地上。
“噗,才夸的你。你没事吧?”
“还……”行。
机工已经缓过来了,正想爬起来,诗人却推了他一把,手按在他的小腿上,一路往上滑,毫不客气地按在他胯间。工装裤下面的那一团东西很柔软,被他没轻没重地捏了一记之后胀大了些。
“我也没什么钱。”机工涨红了脸,半天才吐出一句。
“算你免费。”
诗人笑着说,看他并没有厌恶的样子,伸手解开他的裤链,把东西从里面掏出来,惊讶地抬头看了机工一眼。
……这家伙,堪称壮观啊。
机工的个头没比他高很多,老二却份量不小,去公共浴室洗澡的时候大概会让很多男人相形见绌。他的皮肤很白,性器的颜色也是浅淡的肉粉色,龟头更红一点,看上去还挺讨人喜欢的。
那东西一被诗人的手握住就有点硬了,好像处男一样,随便碰碰反应就很激烈,圈在手里先是缓缓地从根部往上撸,带着琴茧的指腹在敏感的冠部打着圈揉按,蹭过铃口的时候,机工忍不住挺了下腰,捂着嘴发出小声的呜咽。
肉棒越胀越大,在手中一跳一跳的,哪怕不用手扶着自己也能立在那儿,诗人加紧套弄两下,一撸到底,让湿润的龟头从包皮中整个露出来,俯下身“啾”地吻了一下。
不愧是吃草的家伙,那东西捂了一天也没太大异味,只散发出雄性最原始的情欲的气味,给这个呆愣的木头美人增添了一点儿近似动物的印象。
柔软湿润的嘴唇裹着冠部,互相都觉得滑溜溜的,舌尖刮去溢出来的液体,灵巧地绕着铃口打转,突然整根含进去,脑袋上下耸动深喉了几下。
龟头已经顶上咽喉,竟然还有一小截儿没法全吃下去,猫魅族眯起眼睛,拇指和中指圈着根部小幅度地套弄挤压,不时揉捏玩弄底下两颗卵蛋,他吸得很卖力,嘴唇套在肉棒上,晶莹透明的唾液顺着柱身淌下来,把他的手也弄湿了。
机工脸色绯红,身体向后仰,撑着地面的胳膊开始发抖,被一含到底的时候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第一件事是抬起屁股,小心地把身下压着的图纸给推开,这样一个小动作不小心把性器往深处插了插,咽喉排斥地一收,理智上知道自己把诗人弄得不舒服了,从身下传来的快感却让人一阵头皮发麻,手臂上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诗人的猫耳猛地压平,不满地呜咽了一声,把肉棒整根吐出来,咳嗽两声,短促地呼吸着,他跪爬在机工的两腿之间,抬起头来自下而上地看着对方,唇珠和龟头之间牵着一线唾液。
“抱歉。”机工说。
“你一会儿操我的时候也能有这么卖力就好了。”
诗人又一次低下头,微张着嘴探出舌尖,从根部连着卵蛋的系带一路往上舔,故意挑拨肉柱上的血管,甚至还用牙轻轻咬了一口。微弱的痛感猛地一下挑起欲火,机工仰起头来,喘了一声,低声骂了一句达尔马斯卡脏话。
他不认识诗人,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肯做到这个地步,自己那东西长得不小,做深喉想必很吃力,湿热的口腔含着自己的性器反复吞吐,濡湿的鼻息扑在小腹上。
他看起来很喜欢吃肉棒,猫尾在屁股后面愉快地摇摆着,吞吐的动作与其说是服侍,不如说是这个淫荡的家伙把他的阳具劫持来做自己的玩具,随心所欲地玩弄啃咬。
茶褐色的猫魅族好像一只野猫,大胆放浪,理直气壮地向人索取自己想要的所有东西。
“咕、唔……”
诗人的额头上沁出了一点汗水,这家伙怎么回事?还好刚才没夸下海口说什么三秒让你射出来之类的大话。
机工喝了酒,身体反应有点迟钝,尽管觉得很舒服,却没有什么要射的感觉,看见诗人露出困惑的表情,不免有点尴尬,正想说算了吧,诗人用手背抹了抹嘴,骑到他身上来,抓起机工的手,引着他给自己脱衣服。
维埃拉族没什么贞洁的观念,都到了这一步,他也并不扭捏,摘下手套来,剥下诗人的衣服,那平坦的胸膛无疑属于男性,乳首和乳晕却大得晃眼,一侧的乳头上挂着乳环,牵着一截短链,好像暗示别人来揪一下。
“嗯——!”
在反应过来之前,机工已经这么做了,他捏住那条链子,把乳粒拉长,诗人发出一声猫叫似的拉长的呻吟,放松下来,小声地哈、哈喘息。
他本想骂人,但刚张开嘴又是一声浪叫,机工舔上他的乳头,吸住乳晕,整个往嘴里卷,像喝奶似的,舌尖立起拨弄乳尖,另一只手玩弄他的乳环。
要说技巧也没多好,但是他差不多给剥光了,坐在机工的衣服上,明显能感觉到那根热腾腾硬邦邦的肉棒抵着他的肚皮,把前液都蹭在皮肤上。
一阵酥酥麻麻的快感从脊柱窜上来,尾巴竖起来又放下,胸前被舔得一片晶莹,湿润的吻不断往下,亲了亲他的肚脐,兔耳朵尖儿痒痒地扫着他的下巴。
诗人把机工的头往下按,主动把阴茎捞起来,说:
“给我舔舔这个。”
在本该是平坦的会阴部,赫然是一口女人才有的阴阜,颜色熟透了,馒头似的大阴唇紧紧抿成一线,小阴唇上泛着可疑的水光。
机工愣住了,低下头凑近了看看逼,又抬头看诗人,把他的阴茎也翻来翻去地观察了一番,好像诗人是他手下出了问题的机器人;要不是他还有理智,可能会很想把这个人拆开看看。
头顶上传来诗人的笑声,按着后脑勺的手又施了点力,机工嗅了嗅那处,像吸他的乳头那样,叼住探出头来的湿软肉蒂吸了一口。
“咿!……你这家伙,对它要温柔点啊。”
大腿把他的脑袋夹住,兔耳在小腹上蹭着,机工闷闷地“哦”了一声,舌尖挑开阴唇上下滑动,尝到了爱液的甜腥。底下那个小口正不断地溢出水来,软舌钻进阴道里,肉穴敏感地一夹,但哪里能真的夹住灵巧的舌头,只能发着抖任由它像性器一样进出。
“你……你很厉害嘛。”诗人喘息着说。
“我以前听说,这就跟吃东西差不多。”
在密林中,维埃拉一族的生育率不高,为了丰产,为了填补人口的空缺,在你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是男是女的时候,他们就会教导你一点有关性的事。调情要有耐心,用舌头舔舐,把汁水吮出来,用你的耳朵去听对方的呼吸。
有本事的情人只要几分钟能挑起情欲,但他们会把前奏拉得很长,直到对方难耐地用身体邀请你——
“已经很湿了,把你的肉棒插进来吧。”
诗人说。
他用了个荤词,其实机工没听懂,但并不影响理解。如果一个人对着你张开腿,用两根手指拉开自己的穴,就算他嘴里说的是外星语,你也会理解的。
维埃拉族扶着性器对准小穴,龟头很顺利地被吃下了,猫魅族的腿勾上他的腰,脚后跟鼓励地敲敲他的屁股,性器一寸寸地挺入,那东西实在太大,把阴道的每一寸褶皱都撑开、展平了,诗人的阴茎软了一点,很快又重新硬起来,甬道谄媚地收缩着,比口交还要舒服。
机工忍不住挺腰抽送起来,性器一下重似一下地往里顶弄,维埃拉族的性交节奏像兔子一样快,持续的时间却很长,花穴被猛烈的撞击操得软了,诗人高声浪叫着,放松身体,任由性器骤然顶上深处隐秘的肉壶,龟头磨在那道小口上,要插进去一样,持续不断地凿着。
“哈啊、好舒服,顶到——了……”
敏感的软肉清楚感受到硕大圆润的龟头的形状,操一下就好像对准那道小口用力嘬了一下,淫液淅淅沥沥淋在肉棒上,那处本不应让异物进入,因此紧紧闭合;但身体的主人却放浪不堪,被欲望冲昏了头,一味地想要追求绝顶的快感,诗人叫着“用力点,插进来呀”,但当真的被用力反复操干,又会呜呜地呻吟,又像哭腔又像爽得过了头。
宫口被磨得酸胀不堪,一时松懈,让那根插了进去。
诗人浑身颤抖,伸手下去粗暴地揉自己的阴蒂,让机工腾出一只手来帮他打,前后都被刺激着,快感过电似的窜上脊柱,阴道受惊地痉挛,把里面的肉棒吸得舒爽极了,深处的肉壶漏了似的痉挛着喷出一股股热液,随着激烈的抽插被带着飞溅出来。
“啊啊——到了、到了……”
“好厉害……好、爽……唔……”
头脑被搅得一塌糊涂,只能发出些无意义的浪叫,机工被他的呻吟勾得兴起,急切地抽插起来,肉体拍打的声音濡湿沉重,他快射了,鼻息粗重起来。
女穴正处在不应期,生理性地痉挛抽缩,肉刃不得不更加用力才能挺进深处,顶得诗人微微翻起白眼,无人抚慰的阴茎搏动了几下,自顾自地射出了白浊,淋在机工的衣服上。
“怎么样?……唔,你也弄得太久了,刚才给你口的时候,本来想让你射在脸上来着。”
机工动作一顿,又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估计是家乡话。他的耳朵掸了一下,深埋在里面射了出来。
两人一时无言,只剩下喘息。机工活动了一下,半软下来的阴茎从诗人的屄里滑出来,发出噗啾一声,那口穴缩了缩,吐出一股精水。
诗人翻身坐起来,捧着奶子,捏起自己的乳头看了看,链子情色地晃动着。“都被你吸肿了。”他说。
白兔的脸色又是一红,现在理智终于回笼,自己也想不明白刚才为什么抱着一个男人的胸又舔又吸的,他没来得及琢磨,诗人歇了一会儿就骑上来,干脆把他裤子也扒了。
“再来一次,”猫魅族按着他的胸膛,居高临下,“你这裤子太硬了,把我皮都要磨破。”
他指指自己的腿根,那处皮肤格外细嫩,在刚才的性交中被粗糙的布料磨得发红,甚至还有一个方形的皮带扣的印子。
诗人张开双腿,用湿漉漉的屄去蹭机工那根,蹭得硬起来了,就握住肉棒对准雌穴坐了下去。刚才做了一次,雌穴里又湿又松,噗哧一下吞到了底,骑乘的姿势进得很深,龟头直接顶进了还没合拢的宫腔,被子宫套着,大阴唇压着卵蛋,暧昧地磨了磨,还什么都没做呢,诗人就爽得浑身一颤,尾巴竖起来。
“呼……嗯,你别动,我来。”
猫魅族小幅度晃动着屁股,有意收紧肉腔,一寸寸地吐出肉棒,又猛地坐下去,两人都发出一声闷哼。隔靴搔痒地玩了几次,他自己也硬了起来,阴茎上下弹动,拍打着机工的小腹。
机工皱着眉,很难克制住兴奋的喘息,像这样被人按着榨精的感觉很奇怪。满眼都是诗人的裸体,奶头上还留着他咬出来的牙印,乳环上的装饰晃晃悠悠。
诗人用雌穴含着他的阳具,像骑马似的前后晃动着坐他,性器一直插得很深,才抽出一点又被尽数吞下。贪吃的雌穴被填得满满的,每顶一下,身上就泛起一阵酥麻,好像身体的最里面都被贯穿了,已经被操开了的宫口无力防范性器的侵入,像个肉套子似的挂在肉棒上。
“好棒……再来一点,又要——”
“嗯、你这东西,简直要……顶到,胃了……”
诗人吐着舌头喘息,一副濒临高潮的痴态,含混地说着些淫词浪语,骑乘的节奏越来越快,屁股拍打着机工的腿,子宫里不断涌出淫水来润滑,随着交合发出咕啾水声。
那条毛茸茸的猫尾也摇得晃眼,可惜离得太远,没办法拽过来在手中把玩。
机工忍不住挺腰配合他,在他往下坐的时候顺势往里顶,诗人喘得急了,腿也不住发抖,本想休息一下,红了眼的兔子可停不下来,追着往里插,诗人不小心腿一软,结结实实地坐了下去。
“呜——呃、什……”
肉棒干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粗硬的肉棒仿佛能在肚皮上顶出形状,他翻起白眼,呻吟短促地拔高,半途就没了声音,只剩下失语般的哽咽从喉咙里挤出来。
机工感觉身下一热,被什么东西淋了一腿,诗人大汗淋漓,一副高潮得头晕目眩的表情,跌坐在机工的肉棒上潮吹了,爱液开闸似的喷出来。
他一时间咬得很紧,被内射的时候,身体又颤了颤,猫尾很长时间都保持着竖起的状态,顶部微微蓬起,炸了毛。
“哈、哈……”
诗人喘息着,上身伏下去,捧起机工的脑袋和他接吻。唇舌交缠,嘴里还残留着对方私处体液的淡淡咸味,混着唾液被囫囵咽进肚子里,混乱的呼吸间隐约有酒精的气味,夹杂着雪、灰尘,机油和铁锈的味道。
“我……钱,但是……唔、啾……”
机工被一个接一个落下的吻堵得说不出完整的话,诗人直勾勾地盯着他,就像刚踏进门时那样,视线锁定了他,捕猎一般的眼神。这一刻机工才意识到这家伙恐怕根本就是有备而来,不过就这样将计就计,似乎也不赖。
“……如果你没有地方去,我住的房间,再加一个人也行。”
——END——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