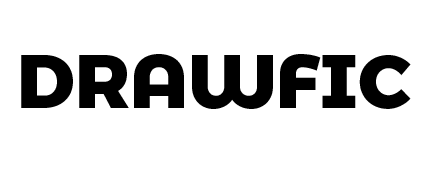标签: 三国; 叡师;
-
作者帖子
-
9 8 月, 2024 9:34 上午 #3531
白鹭洲
参与者*年少东宫时期。
*司马师双性设定。
风动帘卷,孤舟倾覆,将一声声的呼唤淹进雨中,下进苍龙海的支流里。
魏之沉舟,烧了去吧。
于是苍龙海外的河岸上燃起一团火,蒸干了岁岁年年落下的雨。
东宫的翟泉养在苍龙海里,是洛阳城风水最好的宅邸,司马师从雨幕里望出去,记得父亲曾经从楼阁上指着那垂柳间的湖泊说,那是苍龙海,东宫的位置。东宫和永安里隔了一条河,筑起两堵墙,但是为河水留了门,斩不断的水流从东宫牵到司马氏园中,环绕魏都。
司马师那时十二岁,敏锐地发觉了其中的不同,他仰头望着父亲,问道,陛下让您住在东宫边上?
他也记得,司马懿没等他说完,眉头蓦地一蹙,即刻让他跪在面前训诫。你日后交游,在旁人面前绝不能提这句话。司马师不太服气,被父亲的责罚激地回嘴,这有什么好藏的,全洛阳的人都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那就更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司马师跪着,眼见着地板上反的光泛起了夕阳的铜黄,听得身后有脚步,有人在他身后站定,声音清冽。
“免礼。”猜得出那人说话的时候带着笑意,另一脚步声紧随其后,从力度上来说司马师很轻松认出来跟来的是自己的父亲,他抬头的时候一位束发整齐的公子正转头与他父亲说话,“督军,家教严苛?”
他说的话总是很短,甚至略去几个字,不过在他两句提点后,司马懿示意司马师站起来。司马师跪得膝盖疼,身体挪了半步,一时没能起身,反倒像是继续跟父亲抬杠了,显得场面有些许尴尬。不过又是那位公子解了围,他伸手往中阁做了个请的手势,大意是有人在那里等。能让司马懿如此敬重的当然是陛下,他立刻行了礼转身离去,临行给了司马师一个眼神,让他嘴上长点心。
一双苍白的手伸到司马师面前,凉如春寒,有力地将他拉起来。司马师没有怠慢,站稳后先跟他行了礼,在年幼的司马师眼里,他瘦瘦高高,嘴角的笑浅得像在纸上随意划的一道错别字,扯不到眼底。
他不是第一次见曹叡,更不是第一次交谈,建安二十年时,他才七岁,父亲已经开始随魏王征战,他作为长子被诏去邺城,留居后方。那时算不上恣意,尽管有人侍奉与教学,但如履薄冰,行为代表了司马氏的脸面,父亲的一举一动自然也牵动曹家对他的待遇。同窗过的曹叡觉察到他紧绷的状态,一日四下无人时曾对他开口过。
“怎么?”曹叡惜字如金。
司马师想了很久,不知道如何说一个周全的答案,最终回复:“公子,我想我的弟弟。”
那时曹叡也还小,想了半天,邀请司马师去自己家里坐坐,然后把自己妹妹叫了出来,隔着屏风,说我妹妹和你弟弟一般大,你要不聊聊天?
司马师更生气了。
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相处了一段时间,曹叡和妹妹都被魏王带去随军东征,司马师失去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而司马懿也不断跟着征战,他被困在邺城,鲜有能回温县之时。直到改朝换代,司马懿受封督军,他们搬到了洛阳。洛阳荒芜而空旷,宅邸很大,却是穿堂风从南吹到北的空宅,站在楼阁上时,能看到未来这里会被填得多繁华。
他再次见到曹叡,司马懿对他说,此为东宫。
曹叡望过来,一双眼诱人深思又拒人千里,他与所有人隔着一座城。
黄初五年,今年他满了十六。
司马师站在楼阁上远眺雨中苍龙海。
父亲随陛下伐吴,镇守许昌,司马师留在洛阳,早把永安里的宅邸从四壁通风坐成卷帙满墙。这些年他最常见的人反而是夏侯玄,从研讨经书到游园打猎,大多活动是何晏组的,而他和夏侯玄常结伴应邀。司马师并不喜欢这样的场合,更不喜欢何晏,但从父亲临行的嘱托里他读出来,为人谨慎,不代表得闭门不出。夏侯玄还曾带着他去东宫邀请过曹叡,对方却不见,夏侯玄有些不快,司马师却在告别后留下了。
他穿过外园的长廊,见到面向苍龙海的高台上有人读书。
未束发的曹叡依在临湖的坐席上,双臂悬在廊外,攥书一卷,四下风卷起轻纱垂幕和他的头发,和柳花一块缠绕在空中。乌黑的长发衬得他毫无血色,手上的经络和眉骨一样,有墨笔的起承转合。
曹叡的眼睛看向他。
曹叡放下书,撑着脑袋,眉毛挑起来,停顿些许时候,笑了。
司马师发觉自己看了许久的那一瞬,转身跑开了,莫名心慌,甚至忘记去牵马。直到跑到东宫外的车道上,遇到了司马孚从典农署出来的车。他被司马孚提上了车,回永安里的一路,车厢里格外安静。
少去东宫。司马孚的声音少有的低沉,司马师知道叔叔开口极为严肃。
他点头,没有答话,窗上的帘子因为潮湿而颜色变深了,司马师伸手撩开这些绸布,发现外面变天下起了雨。
曹叡的书有没有被打湿?
那日的雨和今日一般绵密,春江泛滥中,苍龙海的水涨得很高,流经永安里的那段变得湍急,司马师忽然见到水中有一叶孤舟,舟中有人仰卧,轻衫散发,未打一伞。司马师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若有人经过永安里的水门还被放行,只能证明侍从不敢阻拦。
是东宫。
司马师猛地从窗边起身,往楼下跑去,他来不及打伞,也不想打伞,他想在小舟被水流送远以前拦住它,从厅堂到花园的路从未这么长,春日草长莺飞,在雨中鸟啼不减,丛生的枝丫来不及修剪,挂住他的衣裳,他奔跑着,枝条勾碎他的袍子,花与叶黏在锁骨上,他跑到岸边的时候显得狼狈。
舟中的人坐起身来,他的长发在雨水中更浓,这两年经历被贬又加封的波折后,他愈发消失在众臣视线里,静谧河水里,他是茕茕孤魂。
雨骤然倾盆直下。
曹叡有些惊异,没想到选了无人的日子还有这样的机缘巧合。看得出司马师生得比他高了,他向他招了招手。
司马师走入水中,小舟晃悠悠离他更近些,他行至舟边时水没到腹部,雨淋得他睁不开眼,他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眯起眼睛来,不得不微张着嘴呼吸。
他们看清了彼此的脸。
曹叡发觉司马师已经不是那个倔强地跪到太阳落山的孩子,他出落得挺拔修长,风雨中沾了一身狼藉落花,反倒显得其于如晦天地间岿然不动。
“你拦我?”
司马师又一次迎着水的阻力,按住了船舷,他能看到曹叡眼里映出的自己。
“我叫司马师,抚军向乡侯长子。”
曹叡的手覆在他的手上,感受到面前的少年因为尽力按住小舟而发抖的手臂,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一只明亮,一只昏暗,光影在眼中碎得没有焦点,与常人不同。人说司马懿的长子风采奕奕,生一双读不出的情绪的眼睛,聪慧又有城府。如此见来,传言是传言,这双眼望向自己的时候,隔着混沌雨帘,他的心思也一览无余。
曹叡探出身去,吻住了司马师。
就凭每次这双淡漠的眼睛看过来时,即刻有潮生。
“子元啊。”曹叡喊他的名字,呼吸落在他唇上。
小舟翻转的时候司马师在水里接住了曹叡,湿透的人在他怀里笑了起来,他的笑轻飘飘的,听不出高兴与否,抱着冰冷的身体,司马师心跳很快。反倒是曹叡拉住了他往岸上走,春寒料峭,冻死在此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没有往楼里走,偌大的花园里,凉亭数个,司马师拉下了四周的帘布,坐在软垫上,伸手替曹叡绞了头发上的雨水。
“不怕被发现?”曹叡任他替自己摆弄头发,没有阻止。
“父亲守许昌,母亲回温县照顾弟弟,或许要接过来住,带走了一些下人。叔父出任于清河,其他人也正当值。”
“多久了?”曹叡抓住了司马师的手腕。
“啊?”他明显愣了一下。
曹叡懒得细问,搂着司马师的脖颈将他从身后拉过来,这次的吻显然和雨中温和缠绵的不同,每次张嘴伸舌头的时候都带着更进一步的意味。洛阳少年春衫薄,薄到雨水刮落一半,纤手勾走另一半。曹叡翻身将他压到垫上,抽走他的禁步,放在嘴边咬断了丝绦,玉碎在凉亭的石板上。他取一段绳结,束起了头发。曹叡舔了舔嘴唇,好像那里留下司马师身上的味道,手撑在对方胸膛上,一边肩随意地耸起,锁骨因此盛着一汪头发上淌下来的雨露,而又随着动作滴在司马师身上。
“你想这样,多久了?”
“我没有。”司马师愕然抬头,近距离撞上曹叡的眼睛,他飞扬的眼角是一轮倒流的月,有一支早开的桂花在蟾宫折断,香味四下追讨司马师此刻离散的魂。他想争辩什么,却只能咽下,曹叡的吻是冲着他身体来的,从脖颈到胸膛,再毫无顾忌到腿间。曹叡从他腿根处抬起眼来,先用舌头舔舐了湿润的指尖。
你真有意思。曹叡的眼睛在说话。他发现了司马师的秘密。
曹叡连口腔都是冷的,和打下来的雨同样的触感,此刻贴在离司马师身体如此近的地方,让他双腿凉得抖了一下。司马师支撑起身体,想要推开曹叡的脑袋,他的年纪还并不太明白怎么去使用身体又怎么去认清现实,只知道曹叡去亲吻的地方于他们两个都是莫大的羞耻,一种僭越伦理道德的耻感。
“公子,不能这样,我知道不能。”
“你知道什么?”曹叡擦了下嘴,“这是为了我。”
司马师不敢再看,但适应了温度后私处传来的被唇舌裹挟的触感让他长叹出一口气,头也微微扬起。这种触感是隐秘的、陌生的、黏腻的,还不适应的时候因为莫名的舒适,条件反射有些躲闪。好比头一次被叶片划破手指骤然收回一般,但次数多了,深陷花丛便能坦然观花。也是这样磨合了许久,司马师逐渐接纳了身下的快感,他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曹叡的舌尖在什么位置,卷走了湿滑的体液,又去逗弄饱满唇瓣中间的花蒂。他的身体在曹叡的舔弄下绷紧,难以放松下来,直到曹叡的手指进入更下方的甬道,一点点摸着内壁开拓。他这才在逐渐进入第二、第三根手指的时候,学会将身体放松下来,但只要手指有什么更大的动作,他又会皱着眉头咬紧牙关,重新尝试容纳这些形状。
良久曹叡见他并不抵触,甚至慢慢没那么紧张,才抬起头来,他垂眼看了会司马师的身体,不知在思索什么,低头在他膝盖内侧亲了亲,将腿压到一边。他自认为自己很少对人这么有耐心,不过这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身体,本也就觉得不出差错才好。
毕竟像现在这样,要进去的,是自己。
身体被真正带着温度的性器填满时司马师一瞬间恍神,他看着曹叡的脸,有几缕未干的头发贴在身上,垂下来的属于他禁步的那一段红绳随着动作摇晃。起初因为尺寸问题还有些隐隐作痛,但对于看着曹叡的脸出神的他来说,这个阶段有些太容易忍过去。很快这一切过度成温暖柔软遍袭全身的情潮,司马师抬了下腰让过程更顺利,腹部因为用力显出更清晰的轮廓来。曹叡的手指满意地滑过他躯体上的肌肉线条,那里鲜有伤痕,是独属于少年的躯体。司马师在抚摸和频率渐快的挺进下呼吸沉重,他自己解开头发,散在地上,以便能更好地仰卧。很快这种惹人沉沦的感觉从陌生变成了愉悦,他的双腿夹住了曹叡的腰,将他拉向自己。此时此刻,他决定不讨厌的这样的行为,尽管还没想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显然身体先一步接纳,而精神上也渐渐有了秘而不宣的依赖。
司马师伸手,扣住了曹叡,手指从他的指缝里钻进去,牢牢地拉住了,向来冷淡的脸上出现了若有若无的满足的笑意。
却见曹叡偏过头,鼻腔里发出一声笑来。
“这就够了?我都没找到位置。”
“什么?”司马师先前因为自己的身体对性一直比较避讳,反倒是不太清楚。
曹叡松开他的手,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另一只手直接按在了刚才反复舔弄的私处,用拇指沾着身下的爱液揉弄他的前处红肿的珠,同时狠狠往他身体上方顶去。刚才手指摸进去时大概确认了方位,此刻便尝试着用了力气,从不同角度去顶撞那个区域,配合着手上的动作。司马师里外两处都被刺激到,嘴里漏出没控制住的声响,甬道骤然缩紧,夹得曹叡也喟叹一声。司马师身体颤抖起来,身体里的雨比亭外的更汹涌,但他被按住肩膀无处可逃,定死在一方情欲的囚笼里。
公子、公子……
他听到自己这样断断续续喊着,耳朵里连雨声都听不见了,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曹叡进出他身体夹带的清澈的涟漪声,还有曹叡的呼吸。他意识到刚才曹叡意有所指,身体给了最明确的答案。曹叡熟稔地找到了那把打开他身体的锁,在他心房里掀了一场漫漶情潮。他的十指都抓着软垫,几乎将上面的针脚扯断,身体弓起来,从无意识地迎合,到逐渐清醒过来,用腰力去控制节奏,一点点将曹叡吃得更深。但试图控制性的节奏,却意味着身体的失控,他的欲望攀爬,掌握了他的思绪,他终于从本心、从自己所需出发。
他睁开眼,看着曹叡,只那么一瞬,就被席卷的快感逼得闭上眼睛,但他知道这是自己想要,自己得到的。
司马师的身体忽地蜷缩起来,他收紧了双腿,整个甬道含着曹叡的性器痉挛着,他伸手推曹叡的胸膛,推开一些的时候身下一股半透明的液体溅到曹叡的腹部。曹叡未等他喘气,将他的手拉到头顶,解下头上的红绳缠住了他的手腕,直接顶进他还在抽搐的身体。
“曹叡!”
多少年没有直呼其名了?那一瞬尊卑罔顾,司马师叫出曹叡的名字来,他被攥着双手,身体承受越线的侵袭,曹叡的长发散落下来,包裹他的身体。
曹叡、曹叡。
司马师不断地将他的名字喊出来,他眉头紧皱,高潮后的身体一次次被作弄最敏感的地方,使得这种触感超出了身体的承载,无尽的浪潮淹没他,吞噬他,他想要反抗,又做不出实际的举动,他清楚意识到身体也在欢迎这样的快感,去汲取不能完全吞下的欢愉。他的身体已经不能躺在垫上,在挣扎和被操弄的过程里早就斜向一边。他听到自己嗓中随着曹叡进出的动作,呻吟和喊出的名字交错进行。
他的脑中只剩下这个名字了。
风动帘卷,孤舟倾覆,将一声声的呼唤淹进雨中,下进苍龙海的支流里。
真有点冷。
这是司马师清醒过来后的第一反应。
曹叡正在用手梳理摇乱的头发,红绳已经落在一旁。司马师沉默地起身,将湿漉漉的衣服又披回身上,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清了清嗓子,最终也没有说话,只是忽然欠身过去,很轻地在曹叡的颊侧亲了一下。曹叡动作停了停,但最终没有给出更多反应,他侧着身子,好像回到了舟中孤魂的模样。
雨势减弱,司马师拉起曹叡,抄着小道往宅里走去,他想绕过主厅,回自己房里找人生了暖炉,给两人都换身合适的衣服。
然后在道中遇到了舟车劳顿刚回来的司马孚。
“……叔父,你不是在清河郡。”司马师一下甩开曹叡的手背到身后去,藏起手腕上勒红的痕印。
“有度支急报才回的洛阳,你……臣见过平原王。”司马孚头还没抬起来对着曹叡一下又压低了,然后在司马师背上狠拍了一掌。长辈拜了晚辈哪有杵着的道理,司马师转了个身马上也跟着司马孚行了礼。
“太守兢兢业业,不必多礼。”曹叡指了指一身湿透的衣衫,“我冷。”
司马孚应声而起,马上喊来人将曹叡接去主房更衣,曹叡错身而过的时候对着司马师抬了抬眉毛,而后消失在了楼梯尽头。
见曹叡走远了,司马孚终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司马师立马在檐下给叔父跪下了。
“干什么呢?”司马孚气结。
“叔父,我错了。”
“你都先斩后奏了你跟我说什么?”司马孚扶住额头,最后手往下一抹,在廊下来回踱步,心里想了一百八十种和哥哥解释的方法,最后决定不说。他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司马师,最后还是一把将侄子拽了起来,“换衣服去吧,别生病了。”
“是。”司马师恭恭敬敬。
最后是司马孚原地哑了半晌,无奈地又长出一口气,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百年后,晋人于永安里北面修武库,掘新沟渠令河流改道,于淤泥中见一腐朽小舟。
什么年月的东西?看朽烂的程度和工艺,并未沉很久。
魏之沉舟,烧了去吧。
于是苍龙海外的河岸上燃起一团火,蒸干了岁岁年年落下的雨。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