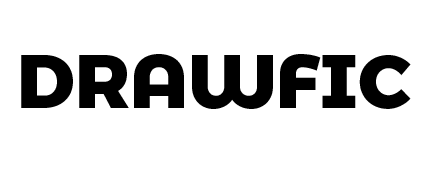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
作者帖子
-
15 6 月, 2024 5:34 上午 #3467
Akr
参与者刚过晌午,天空彤云密布,黑压压在黑衣森林顶上酝酿起一场暴雨。树冠之下一条幽深的林间道蜿蜒指向的一家酒馆早早点了灯,暖色的光透过雾蒙蒙的玻璃往外照出一袭漆黑人影。雷光闪烁之后,一声闷雷轰然炸响,如号令般催促来者推开酒馆沉重的木门。浑浊而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酒香,接着嘈杂人声在他耳畔清晰起来。黑骑环视四周,堂屋里已坐满好几桌人,还是那些熟悉的酡红面孔。油灯的光明明灭灭,人影在墙上晃动。
今天的话题围绕着流传在林区的鬼怪故事展开。当黑骑照例走到吧台左起第二把椅子上坐下,卸下大剑倚靠在柜台边缘时,故事正讲到最精彩的部分:
“那妖异的话音刚落,地上原本散落一地的铁皮碎片便不住颤抖,发出嗡鸣。接着犹如被人用提线操纵一般悬在空中,组成一副完整的盔甲……妖异惊慌大喊:‘不!我们原本是一起的!’那空心的盔甲却举起剑,直直朝妖异劈砍过去。”
讲到这儿,一杯苦艾酒被酒馆的老板,也就是黑骑常联系的这位暗哨推至他跟前。整个酒馆里的人,那些黑骑都一一能叫得出名字的,居住在附近的农户、往来沙都与森都之间的商贩和为人搬东西谋生的苦工,数道视线在抑扬顿挫的讲述里投向黑骑。窥探他掀开面巾,露出的那张疤痕交错的脸。他用一张被割破又愈合过数次的嘴衔住杯口,饮下酒液。上下滚动的喉结吸引着那些颤抖着的目光,直到他把比往常还要苦涩的酒水饮尽,才有人轻轻开口,将故事讲了下去:“那盔甲上泼洒了妖异的血,轰的倒地了。一抹青灰色的魂魄钢铁残骸里飘出,消逝在空气中时,只听见一声哭喊:这是我向你的复仇……”
酒精在舌头与牙齿之间的缝隙中蔓延,黑骑咂嘴将发苦的唾液咽下之际,为那为志怪传说手舞足蹈的人突然噤声。一时间屋子里只剩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雷声裹挟暴雨冲刷而下,穿过震颤的玻璃传来的雨声阵阵。如数千只陆行鸟疾行的纷乱步伐,踏在脆弱的屋脊上似要撕裂屋顶,令人心神恍惚。
意识到刚饮下的酒被下了药时,黑骑的双手已经完全被麻痹了。他眼前发黑,猛地把手拍在桌子上。被挥落的酒杯掉在地上的一瞬间,有熟悉的脚步声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梯冲破雨声,清晰地传进耳中:一轻、一重、一轻、一重……甚至能让人想象到来者的肩膀高低耸动,像群山那样起伏着的样子。铁包的靴子尖在地上短暂拖行一小段,金属在硬物上刮蹭发出来的刺耳声响。有规律的,仿佛钟表时针走向整点时打锤敲击音簧,犹如某种预兆。在抬头的一瞬间黑骑才明白这种声音给予他的熟悉感是从何而来——在伊修加德尚未结束龙诗战争时,异端审判局以维护正教之名对他这样的异端用刑前,那些浸染鲜血的刑具被打磨时,发出的正是这样刺耳的嗡鸣。
“唔……”黑骑欲要呼唤来者的名字,喉咙却仿佛被人扼住一般无法正常发声。抬头怒视时,正是那头熟悉的金色头发映入他放大的瞳孔中。与黑骑的狼狈相比,骑士整个人显得极其放松。他斜倚在柜台边缘,用手肘撑住自己半边身子来分摊曾被黑骑亲手打断的那条腿上的压力。一缕细长马尾弯过颈侧垂至胸前,被他修长的手指随意拨弄。他眯着那双灰色的眼睛,望着已经因脱力而趴在桌子上不住喘息的黑骑,只是安静等待着。只过了数十秒,黑骑便如山般倾倒在地。意识陷入混沌的最后一秒,故事的最后一句重新在他耳畔回响:
“这是我向你的复仇。”撑开沉重眼皮之后,黑骑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完全的黑暗里。暗无天日的房间,连紧闭的门扉与墙体连接的边缘都不曾透进一丝光亮,完全被剥夺对时间、空间的感知能力,好像置身幽暗的深渊。冷得像冰的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花椒香气,唤醒黑骑对某位在石场水车售卖香料营生的商户的全部记忆。那是一对约莫四十多岁的精灵夫妻,曾多次雇用黑骑保护运送他们货物的车队,他们的一双儿女会把在手心攥得温热的金币交到他手上,并邀请他共进晚餐。
因脱力而发酸的手脚不受控制,只能保持着平躺在地的姿势。忍受着肠胃绞痛的同时,黑骑的脑子正飞速运转思考着当下处境与应对之策。然而当他平静下来之后,耳侧却出现了不属于他的呼吸声。
一缕柔软的头发落在他的脸上,接着,一只冰凉的手抚摸在他崎岖不平的脸颊上。
“你睡过去好久。”骑士的语气平静。他的手描摹在黑骑眼下的一条疤上,仿佛在通过这道痕迹回忆故人。
骑士问:“你有没有梦到过去?”
黑骑没有回答。他在黑暗中窥见骑士的轮廓,对方仿佛一个幽灵,冷冰冰地缠绕着他。他听见骑士笑了一声:“要开灯吗?”
黑骑别过头:“我不想看见你。”
黑骑听见骑士肩上的坠饰晃动的声音,骑士大概是点了点头:“好,我也不喜欢看见血淋淋的。”
似乎是在脑海里预演过无数次,骑士解开黑骑盔甲的动作十分娴熟。原本他的视力就不好,在黑暗中反而格外行动自如。他摆弄着黑骑的手脚,像剥落龙鳞一样,一片片把黑骑剥开。随后一一卸下耳坠、项链和指环,再拉开里衬上的绳结,彻底把黑骑脱到光裸。忽略在整个过程中骑士都紧紧扣住黑骑的关节使他无法反抗之外,他的手法温柔得好像在精心处理一具尸体。他把手按在黑骑上下起伏的胸膛上,顺着一条笔直的疤痕往上,指尖按着皮肤,从喉结上滚过。接着掰开黑骑的嘴,搅进他热腾腾的口腔。指节顶开牙齿,压住舌头,顺着上颚往喉咙里勾弄。难以言说的饱胀感令黑骑几欲作呕,但都被骑士扼住喉管压制下去。骑士并起的手指挤进狭窄的咽部,被手撑满的嘴被迫张开至嘴角几乎要撕裂的地步。乃至呼吸都受到阻碍之后,骑士才把手抽出来,又顶进去。反复多次模拟性交,暴力地在黑骑喉咙里搅出一股腥甜。
“牙齿有些碍事。”耳侧开始嗡鸣时,黑骑听到骑士这样说,“舌头和喉咙用起来却很舒服,挤压和推拒我的感觉像是在迎合。”
以羞辱为目的的侵犯才刚刚开始,黑骑已经感觉自己的脑袋因为缺氧而发昏,隐约有失重的感觉了。他开始想,为什么数十年前还在以兄弟相称、亲密无间的人会变得如此扭曲狰狞,为什么超过原本血缘纽带的情谊会转变为不死不休的恨。回过神时,骑士已经抽出手,松开他几乎要被扭断的脖子,让空气重新灌进他的肺里。疼痛使他的眼睛溢出生理泪水,那泪水却被某人冰冷的嘴唇擦干了。
骑士的声音很轻:“你知道吗?那些被你托付了信任的人,听闻你对我们做过的事,都心甘情愿帮我抓你。”
“你……”黑骑的嗓子哑到失声,他反复吞咽调整状态才把话完整说出来,“你威胁那些手无寸铁的人。”
骑士咬着牙:“我要你也尝尝被背叛的滋味,什么手段都无所谓。”
黑骑再次吞下喉咙里的血:“我没有背叛你,我也没有害死过任何人。”
骑士很明显低下头,有更多他的头发垂到黑骑脸上:“你们真的一样固执,但比起一心只想着救人的他来说,你的固执格外可恨。”
黑骑突然笑起来:“你不觉得我们更像吗?你恨着我的时候也恨着你自己。”
他的笑很快止住了,因为骑士把一把刀刺进了他的腹部。
有宗教统治的地区用活祭的方式敬奉神明,作为贡品的牲畜或人被屠宰时需要格外注意第一刀的切入位置。骑士的这一刀就插在黑骑肋下的三角区。骑士的爱人,也是曾与他和黑骑一同长大、一同成为了骑士的兄弟正是因为被刺伤这个位置又没能得到治疗而死的。或许是早已在脑子里预演过数千遍,骑士下手很熟练,细长的匕首竖着往下拉了两寸,一指深的伤口顿时溢出大量鲜血。
黑骑发出一声痛呼,倒吸着冷气连唇齿都开始颤抖。随着骑士继续向下走刀,他能清楚感觉到自己像一条鱼一样被开膛破肚。血液从破裂的血管和脏器里喷涌出去,仿佛抽离灵魂一样的疼痛贯穿他全身。
“我不想杀你。”骑士金色的头发在他溅满了血的脸上被染成深红,“你是这个世界上除我以外唯一一个还记得他的人了。”
“你这个疯子!”血涌进黑骑气管,随着黑骑急促的呼吸涌出他的口鼻,他的话语模糊中带着怨恨,“你——”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随着治愈魔法的光芒开始闪烁,被骑士当做刑场的房间的全貌映入黑骑的眼中。家具陈设、墙上的涂鸦、悬挂在武器架上的三对剑盾,仍旧是数十年前他们住在一起的骑士宿舍的模样。只是蒙上了一层灰,像有雾飘散在空中,把过去美好的回忆与现在隔绝。
“你。”他重复了一遍,似乎他想不起来骑士叫什么了。他无法把记忆中的人与现在面对的人联系在一起,故而嘴拒绝吐出那个曾多次呼唤过的名字。他是个从来不沉溺于过去的人,可是那些记忆在血液流失后逐渐变得恍惚的大脑里涌现,像走马灯一样带着他回到三个人还住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光里。
“我一开始就说过,你不适合做骑士。你脑子里只想着占有,从来不肯承担一点责任。”黑骑喘着气,不断有血涌上他的喉咙,这让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模糊,“我问过你,要不要一起走。”
骑士的刀第三次划开黑骑被强行治愈的伤口,他的手几乎已经握不住刀柄了,血黏糊糊地从他指缝里挤出来。他的回答因愤怒而发着抖:“你就不该离开……”
他们在上次见面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肯困于一隅的黑骑选择离开后,留下的两人中的一个为了救人而死。剩下的这个浑浑噩噩,无法释怀于爱人的死而在久别的重逢时非但不喜悦,反而开始责怪黑骑的决绝。爆发了争吵之后黑骑打断了骑士的腿,没有痛下杀手将是他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因为亲兄弟之间的仇恨,往往只有死亡才能解决。
反复被切开的伤口中流出的血几乎要把黑骑淹没。他躺在生死边缘,像木偶一样被骑士操控,给予不了半分反抗。
黑骑闭上眼睛,骑士的刀也随之停下切割的动作。他把手覆盖在黑骑破烂不堪的伤口上,然后插进去。在温热的液体里搅动时,柔软的碎肉和脏器从他指缝间穿过,这微妙的触感令他颤抖的身体归于平静。他俯下身把额头贴在黑骑的额头上,这让他的姿势看起来像是在虔诚跪拜。脸与脸亲密相贴,骑士依旧无法从黑暗中分辨清黑骑的五官。因此他们的呼吸交融在一起时,他甚至有一瞬间错觉此刻躺在自己身下的人并非黑骑。
回过神时,他已经亲吻上那两片沾血的嘴唇了。骑士站在盥洗室里,水断断续续冲干净他手上的血渍。墙上模糊的镜子里倒映出他的脸,身着布甲的少年望着他银白色的盔甲上红线绣描的十字花纹,与肩头垂下的靛蓝色披风;望着他腰间打满昂贵魔晶石的配剑和盾,还有一张狼狈而憔悴的脸。
当骑士伸手想要触及镜中的自己时,过去的幻象从他已经逐渐无法视物的双眼里消散。面对现实,莫名的愤怒让他忍不住挥拳打碎镜子,完整的一轮圆月瞬间被裂纹切割成无数份,碎得到处都是。甚至有一片玻璃割伤了他的手,他的血流进洗手池里的污浊之中,与他最恨的黑骑的血融到一起。
他没法阻止自己回想过去。憧憬着光鲜的骑士身份而聚集到一起的三人仿佛被诅咒,背叛和死亡把他们分割开后,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这身空壳盔甲。
倘若早知道得到这些的代价是献祭自己曾最珍视的友人与爱人的话……
骑士推开宿舍的门,把灯打开后,赤裸着躺在地上血泊里的黑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爬了起来靠坐到床边,正擦着火柴点烟。火光跳动一瞬,照亮黑骑脸上斑驳血迹。随后烟雾从他嘴角缝隙里腾升,笼罩住那双不曾把目光投向骑士的眼睛。
“在想什么?”骑士走到黑骑身边坐下,他的目光在黑骑夹着烟的指尖与四周游移,“你不该动我的东西。”
黑骑没有回话。他吐着烟,垂着眼睛,好似在叹气。骑士就坐在他身侧看着他手里的烟卷燃烧到中段,心里把数字倒数到二时,再也忍耐不住。他站起来,抄起桌上的水杯就往黑骑头上砸。黑骑闷哼一身瘫倒下去,摔在地上。骑士踩着他的手腕坐到他身上,一下一下继续打他。打到黑骑的脸在一片肿胀凹陷的紫红中分辨不清原本的五官时,骑士才喘着粗气收手。
骑士捡起地上黑骑没抽完的烟,用牙咬着。他抖得厉害的手擦了十几次才勉强擦着火柴,但被血浸湿的烟已经没法儿被点燃了。他转眼瞧见黑骑挤成一条缝的眼皮下的眼睛仍看着他,那双被充血成赤红色的眼白围绕的灰色眼珠,仍傲慢地带有怜悯的意味。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骑士问。
他伸出手。一只按住黑骑的脸,另一只从黑骑眼皮缝隙里插进去。过程很顺利,在黑骑无法抑制的惨叫和咒骂声中,他挖出一双破碎的眼球。
“你!你怎么敢!”黑骑吼叫着,他的面容扭曲,凹陷的眼窝里淌出粘稠的血。如果黑骑没有毁容的话,骑士能在这个详细观察他五官的时机里发现他们的相似之处,从而窥见他们不止是名义上的兄弟,更有血缘亲情。但比起人,黑骑那张脸此刻更像恶鬼。他发出刺耳的咒骂,用尽他在这一瞬间能想到的全部脏话:“……是你!该死的是你!”
骑士用力掐住他的脖子,掐得黑骑的骨头嘎吱作响。黑骑被迫把头仰起来,因痛苦而挣扎着的身体也逐渐平静。骑士一个字也不想听,但仍能看见黑骑的嘴张合着:“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其实是……”
骑士的手收拢,黑骑的话就这样凝固了。世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喘息中夹杂着低低的呜咽声。骑士伏在黑骑像是在颤抖的起伏着的胸膛上,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眶、额头和脖子也开始疼,这些疼痛愈发强烈,就好像他给予黑骑的伤害报复回了他身上。骑士仓皇无措地站起身,却见到黑骑只是分外平静地躺在那儿。新旧伤痕把黑骑的面容变得无比扭曲,可他只是用那双空洞洞的眼窝流着泪。泪水混着血淌出来,像燃烧后融化又凝固的蜡烛,在黑骑的脸上留下两条蜿蜒的痕迹。
“你比谁都清楚我的无辜。”骑士听见黑骑沙哑的嗓音,他伸手捂住黑骑的嘴,黑骑的话继续从他指缝里漏出来。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让人听得极不真切:“你也清楚他绝不会对为救人而死这件事后悔。你恨着我的时候也在恨着你自己,恨那个谁都留不住的你自己——”
“你说得对。”骑士吞下像刀一样刮着他喉咙的唾液,“但这不是我想听到的。”
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伸出手捧起黑骑的脸,魔法像水一样轻柔地包裹住伤口。血液凝结成痂,皮肉与骨骼生长愈合。除了那双眼睛,一切都恢复到能维持黑骑生命体征的底线,甚至骑士都能再听到擂鼓般的心跳声。倘若十年前骑士的魔法有如今的水平,那他的爱人,乃至那些被他迁怒的难民,大概都不用死了吧。
“第一次杀人之后,我的骑士水晶就不再闪烁光芒。仿佛在否定我的所作所为一样,黯淡至今。”他拿来浸湿的毛巾擦拭黑骑的身体,“我做了很多来赎罪。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但凡向我求助的,我都会应允请求,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他的动作很轻,不会牵动那些刚刚被强行愈合的伤口。清洁细致到从黑骑的眼角到腹部,反复被濯洗干净的毛巾逐渐被染成褪不掉的红色,最终骑士的手满意地敲击在黑骑苍白到发青的皮肤上。
“我的剑技不完整,许多事做起来格外麻烦,我不得不花费几倍的功夫去完成别人的委托。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过得很充实。我的脑子被这些没有意义的事填满,逐渐忘记失去你们时的悲痛。”骑士把黑骑抱到床上,床和他那条瘸腿发出嘎吱嘎吱响声,接着他在黑骑身边坐下,“运气好的话,我们永远不再重逢。”
他在黑骑身边躺下,像儿时一起睡在通铺上那样紧挨着彼此。触摸到冰凉的肌肤和僵硬的肌肉时,他意识到黑骑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死了。或许是在扼住喉咙的时候窒息,也可能是因为挖眼后失血过多,在某个黑骑停止发声的瞬间,他的呼吸,心跳和血液的流淌都停止。此刻的他与夜色融为一体,静静等待着腐烂的未来。不再有指责、咒骂,也不再有锥心刺骨的控诉。黑骑承担下骑士全部的愤怒和怨恨,就像十多年前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一瞬间好像有谁从骑士心里狠狠挖走了一块,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下坠感。当他握住黑骑的手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恨已经迎来了终结。而这种恨突兀地烟消云散之时,无法言说的恐慌感把他席卷。
骑士不由自主地牵住黑骑的手,他的指头从黑骑的指缝间穿进去。他摩挲着对方手心的疤痕,头一次开始思考黑骑离开后到底经历了什么。不甘平庸的灵魂选择踏上前往伊修加德旅途后,是在哪一刻决定放下剑盾拿起大剑,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而受伤,又是否曾在某次受伤到濒死之际后悔自己的决定?
死者无法作答,但骑士已经无法克制自己追寻答案的偏执欲望。欲望引领行动,指引他去撬动黑骑的牙关。失去弹性的嘴唇被骑士的手随意拉扯,感知不到疼痛的肉体被划开新的伤口也流不出血液。越发暴躁的手掰碎了一粒牙齿之后,骑士像是彻底着魔,不住地去拔和抠挖黑骑剩下的牙齿。他的呼吸急促,脑子嗡嗡作响,眼前模糊一片,连有几颗牙碎在他手上都数不清。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把拇指插进黑骑的眼窝里,因血液凝固而呈现出乌紫色的皮肤,终于又被他挖出几抹血泪来,仿佛仍在控诉他的疯狂与残忍。
灯把宿舍的墙壁照亮,生锈的剑盾上模糊倒映着晃动的人影。骑士静坐在原地,他望向窗户上钉住木条的铁钉,似乎想从钉头的锈蚀上感受时间流动的痕迹。好像从黑骑死到现在已经过了很久,久到再也没有后悔的余地。被特意封好的窗户透不进来一丝光,分不清白昼黑夜。因此面对内里正在迅速腐败的尸体,骑士反而显得格外从容。他再次用手擦拭黑骑脸上的血迹,仿佛抚摸着建筑上的浮雕那样阅读着黑骑脸上的疤痕。刀伤和撕裂伤把他的脸变得狰狞,但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黑骑的一生。一个在刀尖上滚了这么些年的人,往往死神都会格外偏袒他,否则不会让他背负如此多伤疤还在世间游荡。可惜命运给他安排了可笑的结局:黑骑没有死在战斗里,没有死在伊修加德正教的审判里,没有死于荣誉。他是在被弃置多年的骑士宿舍里饱受酷刑后,以太一点点流干死去的,死得毫无价值。想到这儿,连骑士都觉得有些惋惜。人们热衷于奉承英雄,但黑骑的死,却是他曾救过的那些人亲手造就的。
随着钉子从封住窗户的木条上被拆卸下来的同时,光一块块地投进屋内,照亮隆起土包的地面与满地狼藉。骑士恍然觉得自己已经快忘记黑骑的模样了,揭开面巾后被切割成棋盘似的脸带给他的冲击已经消失,只剩下一种难以形容的怀念。他有些怀念黑骑临到被挖去眼睛时看他的眼神,里面包含恨、还有怜悯,太复杂。就像黑骑最后没说完的那句话一样,难以解读。
“我们其实是……”
我们原本是一起的。
妖异的叫声传进夜风,刮进黑暗中摇摆的树冠之间,化成道道呜咽似的呼啸。
风把云层吹开后,月色如旧。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