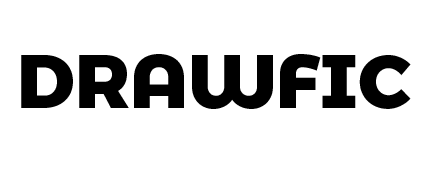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
作者帖子
-
9 5 月, 2024 5:07 下午 #3442
Akr
参与者天还未亮,地面震颤着将一阵轰鸣传进我贴着地面的那只耳朵里,是从甘戈斯运来物资的队伍到达乌特亚前哨的信号。我从营帐里爬出去,只见许多人已经挽起袖子准备帮忙卸运货物。一抹明亮的车前灯刺破黑夜,沉重车轮碾着沙土驶入前哨大门。车队在仓库边停下,我走过去时,一个背着斧子的男人正好从打头的那辆车上跳下来,稳稳落在地上。
我的目光被他吸引,跟着他的步伐走到我们这儿负责保管医疗物资的学者身前。这时我才发现这两人的长相相似,都长着一头打卷的红棕色头发,鼻梁高挺,绿色的眼睛像猫。他们交换了物资清单和仓库钥匙,还有一封信。
他俩的身份并不难打听,尤其营地的赤魔是个热心肠,对我的问题他总是知无不言。他告诉我,男人是学者的弟弟,只是没有和姐姐一样学医而是做了战士。姐弟俩跟随父辈的步伐选择成为义军,如今负责前哨的物资管理。战士偶尔还参与运送,往返后方与前线。
“除了医疗物资,其他所有东西都要经过战士的手。”说这话时赤魔开始朝四周张望,他紧张得有些明显,“你要寄信吗?还是什么别的,你可以找他商量。”
“商量?”我问。
赤魔回过头,他压低了声音:“他做买卖。”
擦着赤魔的帽檐望过去时我注意到,战士在纸上签完字后习惯性地把笔夹在耳朵上。接着他从车前走过,利落地抬起一箱物资就要搬往仓库去。转身时他似有所感,隔着七八星尺的距离直接把头转向我和赤魔站着的位置。昏暗环境下难以分辨战士是否发觉了我的偷窥,我立即向前半步,越过赤魔半个身位让他挡在了我和战士之间。对方敏锐的直觉让我的心猛跳了一下,好在任务紧急,我们得赶在天亮之前把东西搬完,只需要投身忙碌的人群中就能避开探寻的视线。
回到营帐后我叫醒了黑骑和枪刃,按照先前的安排今天我们要去西面巡逻。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早晨还边啃着干粮边系着绑腿的我们当然不会未卜先知到马上要面临的奇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带来的是血肉横飞的、惨剧一般的景色。有炸弹落到到我眼前的那一瞬间,我几乎动弹不得。急速飙升的肾上腺素触发的战逃反应使我本能地举起武器,一剑贯穿身后帝国兵的身体。
皮开肉绽,骨骼断裂,剑柄传来我无比熟悉的震颤。从我第一次杀人直至今日,这种手心发麻的感觉从未消失。
战火点燃了空气,周围的一切好像都烧着了。陆陆续续听见叫喊声,魔法、战技和炮火都无法掩盖死亡的声音。两星时的交火结束,战线往东南方向退了五里。硝烟散尽,我的剑柄已因浸满鲜血而滑不可握,鼻腔里满是烧焦的味道。
黑骑过来拉住我,我转头看向他。
“赤魔死了。”我说。
他死在我面前,离我半尺远的距离。他的血溅在我脸上,到现在还是热的。
黑骑的脸藏在头盔里,此时我分辨不清他的神色,只看到他那双掩盖在阴影之下的眼睛震颤着。我紧紧抓住他的肩,迫切地希望黑骑赶紧说些什么来打破这可怕的沉默,否则在我耳畔回响着的声音就快要压得我窒息。
然而他只是抬起手,用力抹去我脸上的血迹。
“你收编进队的那小子受了伤,”黑骑叫醒我,“你得立马去看他。”
肉身与魔导机械爪的对抗导致枪刃的持枪的右臂直接骨折,在战场上算得上致命伤。意外是,是战士把枪刃拖回来的,我和黑骑都没来得及顾上他。我赶去时战士刚割开枪刃的袖子,枪刃断裂的桡骨刺破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血染黑他的衣服,一路快流淌到我脚边。他头上豆大的汗水混着脸上的灰把脸染得花白,紧咬着的牙连带着失去颜色的嘴唇都在颤抖。
“快,咬着这个。”战士捏住枪刃的下巴,将叠好的衣料碎片塞进他牙关,接着给我腾出位置。我即刻上前,将手覆盖在枪刃的手腕上。在动手接骨之前我对他说:“还好,你这样的情况我少说遇到有五六次了,做这个也算是轻车熟路。”
我看着枪刃,他一时也被我的目光吸引来看我。正是动手的时机,骨头被拉扯的一瞬间枪刃脸色剧变,喉咙里发出一声嘶鸣般的惨叫,整个人坐直起来把头磕在了我的肩上。战士把他按了回去,又把布料塞回他嘴里防止他咬碎牙齿,压着他腿的黑骑更是加大了力道。没有麻醉,连治疗过程都显得格外残忍。我能做的只有尽快将他的骨骼位置复原。骨头是如何从皮肉里刺穿的就要如何被拖拽回去,结合手感和经验将断口对接。接着用魔法催化伤口痊愈,枪刃的骨头、经脉和皮肤会以超出自然愈合百倍的速度生长。而本该被分摊至一个月以上的疼痛会在这一瞬间全部强加到他身上。
枪刃拼命挣扎的样子像一条刚脱水的鱼,但制住他很容易。原本他就瘦,血液的流失同时带走了他的力气。或许是挣扎到精疲力尽,或许是神经切断了对痛觉的感知,枪刃的惨叫没持续多久就停滞了。他动弹不得,只剩一双琥珀色的、像那位硌狮族枪刃一样的眼睛望着我。泪水盈满他的眼眶,浸润爬满血丝的眼白,枪刃却始终没有落泪。
“我会治好你。”我对他说。我紧紧握住他干瘦的左手。枪刃深吸了一口气,仿佛重新活过来了一样。他吐出嘴里的东西,接着长长地、缓慢而颤抖着叹了出来:“我相信您。”部分尸体在确认身份后进行登记,跟着失去行动力的伤员被送回前哨。紧张压抑的情绪依旧没有散去,临时驻扎点的警戒加强了一倍,其余人也要轮换着进行整备。
夜色渐深,休息了两星时不到的黑骑又起来接替了我的岗位,出帐篷时正好赶上放饭。炉灶早就点了起来,坐在锅前操勺的战士仿佛一个生错了地方的大厨。干饼子划开一道把肉罐头煮成的汤浇上去,顿时香气四溢。饥饿感从胃底里被钓起,人群总算躁动出一丝生气儿。战士与他队里的人麻利把食物分发下来,我拿到食物时锅底的汤汁也正好被刮了干净。战士放下了勺子,他拿着自己的那块饼跟了过来,很自来熟地挤着我在远离人群的树墩子上坐下。
“干什么?”我正把饼塞进嘴里,味道确实比直接啃好太多。
“来,尝尝这个。”他声音明快,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少少的一点橙红色粉末。他让我用饼蘸着吃:“前段时间,我们从帝国军手上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有一小罐这个,大概是辣椒粉之类的东西?更像是香料吧,其他人大概吃不惯,但我觉得还不错。”
战士说完还一直紧盯着我的动作,用目光催促我给他一个答案。我没理由拒绝,于是咬了一口咀嚼起来。这调料味道远比罐头煮成的汤要丰富,调和得恰到好处的咸与辣味。隐隐有坚果的香气,把原本就浸润了汤汁而显得湿软的饼衬出一股谷物的清甜。
“对我来说有些辣,但很好。”我如实评价。
战士挑了挑眉:“是吧。”
我笑了一声,像泄了气似的,紧绷已久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人走过什么地方,往往舌头上的记忆更深刻。我的味蕾告诉我这味道与我和黑骑初到远东时吃的第一顿饭有所重合,根据战士的描述,其生产地的范围或许能缩小至多玛。同样是被帝国殖民的行省,那里的局势复杂程度不比博兹雅差。
“你是博兹雅本国人?”我问战士。
战士点头:“是,我是在堡垒出生的。”
我吃完最后一口饼:“我原本还以为博兹雅本土基本上都是硌狮族,来了之后才知道这里什么人都有。”
“哈哈,当然还是硌狮族占大多数。不过在加雷马占领博兹雅后,这里的人种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了。”他转过头,朝伤兵休息的帐篷看了一眼,“义军里还有加雷马族呢。”
“第四军团里也有艾欧泽亚人,人各有选择。”
战士眯起眼睛,有一瞬间我都以为他的瞳孔要像猫那样收缩起来:“阵营不同就是敌人。”
我没说话。战士一坐下来我就知道,战士是来试探我的。刚来博兹雅就弄丢了队友,后续却又在战场上表现突出,这很难不引起义军的注意。
僵持几秒后他另起了个话题:“你的治疗魔法比我认识的骑士都好。快赶得上我姐了。”
“只是一股把人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执念而已。”我摆手,“你的厨艺也是我见过的战士里最好的。”
“你见过几个战士?”
“哪数得清,而且说得上话的就你一个。”我问他,“你多大年纪?”
他脱口而出:“正好小你两岁零三个月。”
他急于向我表明他调查过我这件事让我一下子愣住了。我顿了顿,对他说:“你让我想起一些故人。”
战士挑眉:“什么故人?”
我笑起来:“在伊修加德时我曾和异端审判所的审判官们打过交道。”
“你的意思是我说得太明显了。”他很快明白。
“谈判的过程要忠于谈判的目的。”我凑近他,压低声音,“如果你在想亲近我的同时还想要试探我,那你说出来的话就会不伦不类。”
战士没有避让,我们保持着这个近得格外暧昧的姿势。他没有显露出恼色,反倒将手肘支在腿上,弓起身子,脸更贴近我,平静得好像一切仍在他掌握之中。我嗅到他衣领上的烟草味,牵肠萦心的气味撩拨得我嗓子发干发痒。在来博兹雅之前我仍有极重的烟瘾,毕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用大量烟草逼迫自己保持清醒。我忍不住咽了口口水,主动退让开,战士也松了口气。我说:“义军虽然没有规定禁烟,但烟草在战场上也算是稀缺物资吧。”
战士闻言扯了扯自己半敞着的大衣,然后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黄铜色铁盒。铁盒边缘已斑驳生锈,但上印着“双鹰”的加雷马字依旧清晰。
“明码标价。”战士的语气轻佻仿佛引诱顾客的奸商。
我从里掏出一颗金珠放在他手上,但他刚伸手来接时我便顺势将他手握住。战士吃了一惊,明显想抽回手而不能,反而被我抓住时机握住手腕,彻底陷入挣脱不得的境地。沉甸甸的金珠隔在我们之间,随着我与他拉扯的动作滚动在他腕骨附近的位置并划出一个不规则的圆。战士明显在这一瞬间紧张起来,他读懂了挑逗下的警告意味——腕部薄弱皮肤下是动脉和手筋,他现在完全处于我的掌控之中——他的身体绷直,背上的斧头都随着身体的动作硌在他腰甲上发出响声。直到我抬手按住他另一只手上的烟盒:“金价昂贵,你的烟草不值这个价。得用别的东西来补。”
他终于恼怒了,一把推开我。我就势收下烟盒,战士也怒气冲冲地拿到了他的报酬。他的情绪转变之快令人咋舌,我只将手上的烟盒当战利品炫耀般晃了晃。打开后里面仅五支香烟,可见我的报价不虚,完全够他再为我点一次火。
“就这些。”我笑了声,将烟衔在嘴上。
“就这些,再没多的。”战士迅速平复好心情,恍若无事发生一样擦着火柴。光一下子照亮他的脸,冷硬的面部线条反衬出他眼底的躁动。等一股白烟随着烟丝被燃起而升腾时,他已经藏好了所有情绪,恢复成我第一眼见他时的模样。
义军在征兵时几乎不作任何背调,扩充人数来填补正面战场人数上的空缺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也算是兵行险招。第一次作战时秘密处决掉一批奸细后,义军将剩下的人简单划分,可信任的给予升迁,形迹可疑的需要高度关注,而我和黑骑介于二者之间。显然出众的能力令上面的人难以狠下心来舍弃,因此派遣任务给即将到前哨的战士,让他作出判断。
太年轻,太优柔寡断。战士是,现在的义军也是。
我叹了口气,我决定告诉战士点什么,避免他费尽功夫却一无所获——实际上,我的过去没什么好隐瞒的:“我在做雇佣兵之前,曾在乌尔达哈的银胄团任职。我在沙都长大,穷苦人家出生,无父无母,只有一个弟弟……”
我尽量把语速放慢,果然战士又被我的故事吸引,不自觉放低了呼吸。我抽了口烟,接着讲到:“四年前,他被叛国者害死了。”
烟草燃烧出浓郁香气,笼罩住我的视线,一片白茫茫的雾色被手挥开之后我看见一张熟悉的脸。鲜血覆盖,他的五官也随着记忆流逝而模糊,但额角那条练习剑术时留下的疤仍旧鲜明。他的目光隔着四年之久从过去看向我,把我带回那个寂静无声的夜晚。我甚至听见他的呼吸在我耳侧响起,近得仿佛一转头就能与他紧紧相拥。
“你靠我太近了。”我对战士说。我揪着战士的头发把他按进他独住的帐篷里的睡袋上。他红棕色的头发像狮子,像火,灼烧着我的眼睛。令我不禁加大力道,甚至伸手去扼住他的喉咙。战士主动仰起头,他透亮的绿色眼眸锁在我脸上,我没有在其中搜寻到一丝畏惧。甚至他的嘴角勾起,显然已经兴奋起来。
他的挣扎很有力,迫使我不得不去锁住他的关节来限制他的行动。肌肉虬结的手臂抓握住我的手腕,似要把我像钉子那样拔除。然而我现在正被一股无名燥火支配,完全不想与他再周旋拉扯。他的喉结在我掌心像那颗金珠一样灵活地上下滚动,彰显着他在窒息前的游刃有余。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觉自己的双腿无法动弹,手也使不上力。这时他的眼球才开始震颤,与那逐渐发紫的面容格外相衬。与此同时,我的控制欲和支配欲得到极大满足,团积在心口的一股郁气也消散大半。越是听到战士因窒息而发出呃唔呻吟,听到他的骨头在我手下扭拧发出咯吱响声,这种畅快的感觉越是明显。就快到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甚至比我预估的还要长上半星分,松开手掌的那一刹那他猛地吸一口气,喉咙里快速通过通过空气时发出低吼一样的声音,脸色骤变发红,像临近暴怒的野兽。
“我要剁了你。”
我给了战士一个缓过来的时间,等他暴起一拳砸向我时,我躲开他的进攻并与他撕打起来。狭窄的帐篷不利于发挥,战士没有如他所言去掏斧子,而是和我紧紧抱着,摔跤似的滚作一团。在不断调整姿势的间隙战士刚又被我抓住手,就张嘴用牙来咬我。他的牙比不上硌狮族的锋利,但颌部格外有力,咬住我的颈部便不松口。尖锐刺痛传来时我掐住战士的肩,把他用力摔出去。手抚上脖颈后,汩汩鲜血从我指缝流了下来。
在战士再次扑过来的一瞬间,我抽出剑。剑从战士腰侧刺了过去,划开层层叠叠衣料,刚好留下一道一指长的伤口。恰到好处的深度,带来的疼痛足够唤回他的理智。
我走过去,把手上的血抹在战士的嘴边,他一下子跌坐到地上皱着眉望着我。我把剑搁在他肩上,剑尖距离他脆弱的颈部动脉仅几寸距离:“前戏结束了。”
俯下身吻他时,战士主动张开了嘴。舌头舔舐他带着甜腥味的犬齿仿佛擦拭锋利刀刃,他满足地眯起眼睛。慢慢地我开始解开他的大衣,他顺从地脱下衣服,把上半身暴露在昏黄油灯下。大大小小的疤痕铺陈在他结实肌肉撑开的光滑皮肤上,他很乐于展现这些疤痕,拉着我的手顺着纹理抚摸。这些纵横交错的肉瘤像铭文,实际组合起来并无深意,只是让我判断出他至少有三次经历生死之劫。大概是从鬼门关里爬出来过,对腰间那道小伤也并不在意。只是伸手来解我的衣服,不过我所能展示给他的只有正心口上的一道疤。很短,两星寸长,时白银单手剑刚好把剑尖没入皮肤能留下来的痕迹。再往前,恐怕就是切开肺叶、割断经脉,给予刺穿心脏的一击了。
战士的手涂抹着自我颈部伤口流淌出来的鲜血,在那道疤上比划抚摸。他没有问是谁干的,等他收回手,我便抬起他的腿向他股缝探查。他的性器早已勃起,马眼吐出清液,颤巍巍立在空气中等待着人去抚弄。我想他在床上是习惯被人侍奉的,于是一手箍住他阴茎根部,收紧虎口按压撸动。另只手顺会阴而下抚弄他紧涩的后穴,从那明显没被进入过的褶皱里挤出一寸空隙。
战士哼哼唧唧的,没说舒不舒服,只是抬手丢给我一盒润滑膏。盒子里的膏体余量不多,全挖出来后涂抹在他身上被体温融化成黏糊糊的液体后勉强够用,接下来就是不算顺利的扩张。战士已经尽力在配合我,他将腿缠在我身上,腰往下塌,放松肌肉容纳我的手指。温热的肠道从干涩逐渐被摩擦至湿滑,褶皱的穴口也是逐渐被打开,露出里面的殷红肠肉。
“进来。”战士抬手揉捏了一把自己的胸部,暗色的乳晕晃得我眼睛有些晕。
“你不怕疼就好。”我随即抽出手,扶着阴茎抵住他穴口往里推挤。在他说出更多话之前我咬住他的嘴唇,手指穿进他早已汗淋淋的发间把他扣住,与我缠绵交吻。战士的吻技娴熟,唇舌之间的进退游刃有余,勾弄着彼此交换着唾液,溢满了似的从嘴角漏出。他不肯闭眼,玻璃般透亮的绿色眼睛里盛着生理泪水,倒映着我贪婪的面容。而他的目光只在喘息间微微颤动,色情得好像他已经被我干到失神。我的身体经受不住这种撩拨,只挤进去半截的阴茎硬得更厉害,甚至不顾被抗拒的穴肉箍得发疼卯着劲儿往里头钻。
战士身体发烫,按着我腰部的手也发烫。他硬挺许久而不得抚慰的老二夹在我们腹部去反复摩擦,在我整根没入的瞬间高潮。滚烫的精液直接喷溅出来,空气中顿时弥漫一股腥气。他张开嘴,一时间忘记作出任何反应,只是被我摆布着大张开腿,开始承受我毫无收敛的抽插。
“唔,不,啊啊……你——”战士用他们博兹雅的方言骂我,很像是兽类咆哮一般的语言,用人族的声带发出时显得不伦不类,甚至很难听清他到底说了什么。我按着他的腹部,顶着他深处的软肉反复碾磨,接着把耳朵凑近他嘴边。我分辨出几个略显粗俗的单词,一般用作辱骂或呵斥,没过多久他的语气都软下来,句子也变得复杂,甚至夹杂了“求你”这样的话。
“我能内射吗?”我扶着战士让他翻过身,抬起他的屁股后入进去。他的肠子已经足够湿润了,软软地吮吸着我。我恨不得就这样深埋在里面,再也不拔出来。但同时我又急切地想发泄在他身体里。如同打上烙印一样,我像他咬我那样啃咬他的皮肤。耳朵贴在他背上时,我听见战士的话像项链上的珍珠似的,断断续续蹦出来:“你,最好,呃……别。好深,太快了……”
我扇了他的屁股一巴掌,力道不大,毕竟不能让人听见。战士一下子没了声音,他把头埋进手臂里,腰往上顶了顶。我把他拉扯起来,按在旁边他办公的矮桌子上,手伸下去撸动他再度勃起的阴茎接着操干他。明显有液体顺着他大腿内侧的线条滑落,而我们交合的部位更是已经泥泞不堪。他的肠肉被连带着往外翻又推进去,周围堆积着绵白色的泡沫,是射进去的精液与润滑、汗水混合在一起被搅弄的产物。像海浪,一波一波把战士推向他不可承受的高潮。
我喜欢他颤抖着发出类似呜咽声音的模样,整个人像困兽一样瘫软在地,接着蜷缩起来。他身上多了些新鲜的吻痕,从脊背到我随手治愈好的腰侧,穿插在疤痕之间反而不显得突兀了。夜色幽深,他已精疲力尽,躺在我身侧,左手紧紧扣着我的手。我闭上眼睛,他来抚摸我的脸:他拨开我的头发,拇指顺着眉骨划出一个弧度,在太阳穴的位置停留数秒后直接跳跃到被他咬伤的后颈,接着顺着血曾流过的位置向下,抚摸上我胸口的疤痕。
我几乎能想象到他正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
“谁做的?”他哑着嗓子,轻轻地笑起来,“我替你报复回去。”
我也笑起来。我回答:“是他。我弟弟。”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