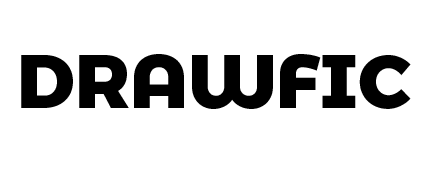-
作者帖子
-
16 9 月, 2024 4:10 下午 #3545
犯罪嫌疑人葵某
参与者再次踏上伊修加德的土地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恶心。
这座城市里的某两个混蛋给予了我生命,却没好好养育我,任由我像石子一样在污雪泥水里打着滚长大。我曾经恨他们,现在好了些,甚至有点期待他们找上门来,毕竟我可是萨雷安魔法大学最出色的毕业生、公认的天才、前途无量的贤者,我有能力也有手段报复他们……前提是他们找上门来。
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来接我的人是某位贵族派来的,他的腰弯得很深,我斜睨着他,把绷得酸痛的腰又挺直了些。老头子不记得我了,倒也正常,毕竟他赶走的乞丐多如牛毛,我只是其中之一。“备车,去天钢机工房。”我把行李递给他,他双手接过,没有任何迟疑就应下了我的要求。
车厢微微摇晃,向着天钢机工房平稳驶去。越是靠近那个人,我的心跳就越快,我说不出催使它快加跳动的情绪是什么。紧张、兴奋、还是恐惧?我太多年没见过他了,记忆中的脸模糊不清,我只记得他的笑容,还有他一次又一次从怀中拿出来的,还带着他的体温的食物。这烂好人啊,明明自己都饿到脸颊凹陷,却还愿意把好不容易弄来的吃食分我一半。我在衣服上擦了擦汗湿的手心,忍不住深呼吸了几次。马上就能见面了,该说些什么呢?拥抱会不会太过热情了?他不一定能认出我,不,他肯定能认出我,我可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唯一的朋友……
车停了,我推开门,步伐轻快地走入了天钢机工房。我看见我唯一的朋友被一大群机工士围在中央,他正在笑。
他长高了,小时候消瘦见骨的身体抽长了一截,脸颊也不再凹陷,逐渐展现出精灵族特有的美貌。他现在肯定能吃饱饭。我这么想着,本能告诉自己应该觉得欣慰觉得开心,舌根却泛起一股苦意,像是吞了一大口浓稠的黑水。他身边围了好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个叫斯特凡尼维安的的男人也在。斯特凡尼维安,我知道这位少爷,我提前调查过天钢机工房,知道斯特凡尼维安就是天钢机工房的工房长,连他都在询问我的朋友是如何研发出新型火枪配件的,而我的朋友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的知识,他得到了好多赞扬和钦佩。他自始至终都没看过我一眼。
“你好,请问你找谁?”
身旁的声音唤回了我的理智,我下意识看过去,那姑娘像被吓到了,身子一缩,还往后退了一步。我闭了闭眼收拾好情绪,但嗓子依旧有些干涩:“麻烦你帮我喊他出来。”
我没说是来找朋友的。单方面的热情太失态了。
机工跟我回到了车上,我没错过他迈入温暖车厢时脸上一闪而过的羡慕。我与他对面而坐,他拘谨地看我,看着看着,眼里的疑惑渐渐被惊喜取代。
“是你!我的战女神啊,居然是你!”
机工一把攥住了我的手,很用力,我觉得手背有些疼。
“我刚才就觉得眼熟,但是没敢认。战女神在上!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了?萨雷安大学的学业辛苦吗?带你走的人对你好不好?我的战女神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机工一直在重复战女神的名讳,可我知道这只是伊修加德人情绪激动时惯用的口癖而已,被风雪割过肉的人不会是虔诚的信徒,我和他一样。我低头看着他的手。精灵族身材高挑,手也修长,机工细瘦的手指上有很多疤痕,圆形的,扭曲的,细长的,我是治疗师,大概能猜出这些伤口的来源——子弹、火烧、刀割。
我的朋友……你一直在关心我,可你过得怎么样呢?
“我很好,一切都好。”我反握住他的手,慢慢攥紧,“你呢?”
机工咧嘴一笑,灿烂的笑容晃花了我的眼。“我也很好!你走后没几年我就遇到了天钢机工房的人,他们不嫌我年纪小,愿意给我一份打磨零件的工作,我这才发现自己居然挺有天赋的!”他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我现在的工资能买300根长棍面包了!而且还有租房优惠,可以在九霄云舍租个长期房间……”
机工事无巨细地说了很多,我也收集到了很多有用信息。新技能,新工作,他当然也交到了新朋友,他说自己终于对未来有了期待,他生活得很幸福。我一直静静听着,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大概没有。心跳再次加快,那块血肉几乎快要从我的喉咙里挤出来,而我现在知道了它加速跳动的原因。
恐惧。
数年时光将我们分割开来,我与他之间有了巨大的鸿沟,不是学历和身份,而是他的世界正在变得丰富多彩,我却还留在原地,攥着他给我的温暖像被丢掉的狗一样绕圈。我有钱了,被其他人尊敬着,曾经用拳头把我赶走的老头子现在对我卑躬屈膝,我穿着最华丽的衣服,坐在温暖的车厢里,却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
他怎么能抛下我……他凭什么抛下我……
“嘶!”
机工强行把手从我的掌心里抽走了。我看见他的手背上有很清晰的白痕,他的皮肉被我掐的暂时失血。我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吗?
“你还好吗?”他小心翼翼地问我,我摇了摇头。“没想到伊修加德还是这么冷,可能有些着凉了。”我咳了两声,他立刻露出了关心的表情,我适时提出了请求:“你知道的,我在这边没什么朋友……你能来照顾我吗?”
他答应了。我的机会来了。
穹顶皓天的房产可不便宜,即便是最普通的小屋,购买所用的金币也足够十个家庭吃喝嚼用许久,但对贵族老爷们来说,这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礼物而已,送给我这样根基浅薄的人正合适。房子已经装修好,各项设施一应俱全,连衣服被褥都准备了好几份,我谢绝了管家要派人来照顾我的提议,带着机工入住了这间小屋。
只有我和他,就像曾经的我们蜷缩在云雾街的角落里过夜那样。只有我和他。
机工最开始还有些拘谨,不过在我表现出恰到好处的“虚弱”和“依赖”后,他就顾不上其他的了。在他眼里,我又变回了病弱的孩子,需要人仔细照料,擦汗喂药,把温水端过来,抵在唇边一口口喂下去。我们这样的人都很害怕生病,生病就意味着死亡靠近,毕竟买药很贵,医院也不会接诊我们这样的孤儿,哪怕已经成为大人,恐惧依旧深深刻在我们的骨头里。所以我的装病很成功,他照顾得越细致,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就越近。
又是一天晚上,我早早躺下,却始终无法入眠。我翻了个身,睡在我旁边的机工立刻睁开了眼睛。
“你要喝水吗?还是又开始发烧了?”机工问我,说话时声音含糊,睡意很重。我慢慢起身,拿起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只是有点口渴,没事的。”我喝下一半水,把杯子递给他,“你喝吧,不然就凉了。”
小时候的我们经常分享食物和干净的水,那些习惯还在,机工很自然地喝光了剩下的水,把空杯放在另一侧柜子上。一分十二秒后,他睡着了。
我嚼碎藏在臼齿后面的解药,苦涩的粉末混着唾液融入血中,萦绕不散的睡意很快就消失了,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醒。机工躺在我身边,很安静,处于深眠中,虽然他还穿着一套丝绸制的睡衣,但对我来说,此时他比刚出生的婴孩还要赤裸。我深呼吸了好几次才冷静下来。
给机工下药是我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我要检查他的身体。
壁炉里的柴火尚未燃尽,偶尔发出噼啪轻响,像是有人在为我的恶行鼓掌。我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甚至称得上恶心,可我依旧要做。他的身体完整吗?皮肤平滑吗?会有伤疤吗?我解开机工的衣扣,他依旧沉沉睡着,双臂自然而放松地搭在身侧,哪怕胸口暴露在空气中也没有任何反应。是的,完整,皮肤平滑,腰侧靠近胯骨的位置有一道细小的伤痕,看起来只是刮伤。我用手掌盖住那道疤,感受皮肉的微微凸起。可怜的孩子,我不在的时候他该如何处理伤口?这位置很别扭,他一个人要怎么包扎呢?要是我在就好了,治愈以太对这样的伤口效果最佳,只要一个简单的治疗法术……
够了,别再想那些道貌岸然的事情了。我只是想抚摸他,亲吻他,将我最珍贵的友人紧紧抱进怀中而已。在我第一次了解到人类的身体构造,知道性交,知道性快感这东西的存在时,我第一个想到对象的就是他。书本上简单的插图有了更具象的画面,解决欲望的枯燥过程也必须佐上他的面容,我对他的欲望,对他的渴求,我对他的……对他的……
……爱。
我爱他。
壁炉里的柴已燃尽,房间被黑暗笼罩,逐步靠近的寒气却没能侵染我的身体,一股热流开始在我的腹腔内翻涌。我俯身将脸颊贴在机工的胸膛上,听着他平稳有力的心跳,不知不觉间咧开了嘴。
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终于能拥抱你了。或许还可以再做一些更过分的事,夜晚很长,药效也会持续很久。
我吻上了他的唇。
干燥的唇瓣逐渐被唾液润湿,我撬开他的牙齿,听到轻微的咕啾声,只觉得无比悦耳。他没有拒绝我。我自动忽略了他还在沉睡的事实,动作逐渐肆意起来。亲吻加深,舌尖缠紧,我舔舐他的上颚和齿根,将他的口腔仔仔细细扫荡了一遍,他好像没有和人接吻的经验,这些地方都很敏感,稍一拨弄就会让他发出含糊的呜咽,那是深眠都拦不住的本能反应。这是我的第一个吻,也是他的,我变得格外兴奋,甚至比第一次操控贤具悬浮起来时还要兴奋,这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亲爱的,亲爱的……
下身的胀痛已经强烈到无法忽视,我把手伸进裤子,然后,盯着他的脸。
他的的确确躺在我面前,双眼紧闭,浓密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不用再有更多接触,只是看着他就能让我性欲高涨,阴茎兴奋得几乎在微微抖动。我粗喘着,跪伏在他身上套弄自己的性器。疼痛和快感几乎同样强烈,我任由自己享受偷来的欢愉,喘息着等待高潮降临,可总是差那么一丁点距离。是了,幻想中的性交对象就躺在我面前,身体怎么可能会轻易被满足。我垂眼看向他的小腹,脑内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些画面——他的双腿被我掰开,露出身下浸透汁水的肉穴,我挺腰抽插,把硬得发疼的阴茎往他屁股里狠顶,他会发出呻吟,双手抓紧床单,腰背绷直了往上抬,露出沉溺于欲望中的痴态……
可那些都是泡沫一样的幻想,我的朋友依旧在沉睡,双眼紧闭,呼吸平缓,虽然他的上衣已经被剥开,但裤子还好好穿着,性器也没有任何反应。我舔了舔嘴唇,扶着他翻身侧躺,轻轻扯开了他的裤子。
精灵族身高腿长,身材看似消瘦,臀肉却比我想象中还要挺翘,贴上我小腹时的触感让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吟。欲望和渴求同时得到了满足,我再次抱住他,硬热的性器顶进他双腿之间,开始在他腿根的软肉挤出的缝隙里抽插。这种行为比任何制幻药物带来的欢愉都要让人上瘾,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牙齿,在他身上啃出一处又一处渗血的齿痕。疼痛扰乱了他的安眠,他的嘴唇翕动,缓缓挤出一个冰冷无情的单词。
“不……”
我像是被丢进了雪地里,毛孔张大,浑身冷汗淋漓。这个轻飘飘的字把我从美梦中惊醒了,欲望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我滑稽地袒露着下身,逃跑似的往后退去。
他的睫毛抖动几下,回归了平静。
这样不行。将以太凝聚在手掌上,为他治疗伤口时,我这么想着。我要的不是一只性爱人偶,我想要他的全部,要他用深情的目光注视我,回应我对他的爱意。我想起曾经在禁书库看到的法术,那法术效果很好,不难,只是需要一样东西——施法人的决心。
以太开始向外扩散,化作繁复的纹路在机工的皮肤上蔓延,然后向下浸透,融入他的身体里。一股玄妙的链接将我和他的灵魂捆在一起,牢牢打了个死结。他是我的了,等太阳升起,他从梦中醒来,就会给我最热情的回应。
我拥有了很长一段好时光。
机工向天钢机工房请了假,之后就正式搬到了我这里。一周后,他的朋友来找他,对他的不告而别表示担忧,机工回应得很好,只说自己太累了,正好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我在他们交谈时走出去,搂住他的腰,在他脸上落下一个吻。
“不帮我介绍一下吗,亲爱的?”我笑着说。
难以言喻的尴尬让空气都变得稀薄了,机工结巴了好一会儿才说出我的名字,说我是他的“恋人”。他的朋友用一种古怪的目光看着我,充满审视、疑惑和警惕的目光,我并不在意,我只在意机工的反应。
“我……我马上就回来,你等一下。”
他敷衍地亲了亲我的唇角,把我推回门里。
房门合拢,外面投进来的光线逐渐变得狭窄,我的身体也跟着一点点冰冷下去。机工没告诉那些人我的存在,他在避险,想和我拉开距离,那是连禁术都无法抹除的本能。没关系的。我回到沙发前坐下,从桌上的木盒里拿出自己准备许久的东西,一条长鞭,牛皮鞣制,三股编成,看似柔软的鞭身其实有很强的韧性,落在人身上能带来无法忍受的疼痛,以及几周都不会消退的淤青。
我用鞭子轻轻敲打另一只手的掌心,等着机工回来。
他没让我等太久,很快就急匆匆地进来了,他看到我时明显怔愣了一下,然后迈步的速度越来越慢,几乎是挪动着走到我身前。这一周的投喂让机工长胖了一点,丝绸衬衫紧贴在他的身体上,微微勾勒出腰腹软肉的弧度。那一层肉手感很好,我摸过,掐过,咬过,乐此不疲。
但我今天有了新的想法。我拿起长鞭,指向自己脚边的地毯。
“跪下。”我对他说。
他没有任何迟疑就跪了下来,仿佛做了无数次,他也的确做了无数次。我说过,我拥有了很长一段好时光。
衬衫落在地上,机工赤裸的上身暴露在空气中,我站起来绕着他踱步。伊修加德常年被冰雪覆盖,机工捂在厚衣服里的皮肤白得晃眼,他身上那些淤青和咬痕被衬得格外明显,我用鞭子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立刻会意,把双臂背到身后,挺起胸膛。他的乖巧安抚了我,但还不够,我了捏紧鞭子。
皮肉被抽打的脆响还在回荡,机工的闷哼就把前一个声音压了下去。这一周里我听见了许多声音,他的呻吟、喘息、哭叫,以及一遍遍喊我名字时候极度颤抖的尾音,真是怎么听都听不够。鞭子再次挨上他的皮肤,抵住他的乳尖,这里被我刻意鞭打过,不用太过刺激就会挺立起来,他的视线跟随我的皮鞭移动,然后缓缓抬起头,看向我。
啊……真可爱……
他的双眼里没有恐惧,只有期待,这具身体被调教好了,他适应了疼痛习惯了快感,变得格外贪婪,毫无底线的向我索求一切。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目光,我相信其他人也没见过,这是只属于我们的秘密。身体仿佛泡在了温泉里,我被幸福感轻飘飘地托起来,于是下手的力度更重了。
机工士们善于使用各种威力强大的机械,那些东西不轻巧,所以他也并不瘦弱,可这样一个能把我轻松打倒的男人,此时却跪在地板上,挺起胸膛承受我一次又一次粗暴的鞭打。紧实的胸肌遍布淤紫,横横竖竖的鞭痕在他身上勾勒出可怖的画卷,机工的腰侧和脖颈也在鞭子照顾的范围内,甚至脸颊都挨了一下,浮现出肿胀泛红的痕迹。我用右脚分开他的膝盖,把他的睡裤踩下来,意料之中的,他的性器早已挺立,跟他的身体一样颤巍巍地发着抖,茎头滴落的前液扯出几缕细长的银丝。
“呵……”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在胸腔里回荡。
“你想要什么?”
机工膝行向前,迫不及待地把脸埋进我胯间,他的双臂依旧乖巧地背在身后,只用牙齿叼着我的裤子往下拽,然后含住我的性器。比起生理上的快感,他这幅极尽讨好的模样更能取悦我,我把鞭子搭在他颈后往前压,让他的头埋得更深,把我硬得发疼的阴茎完全吃下去。真可爱……
机工被撑得喘不上气,双眼很快就盈满了生理性的泪水,胸部起伏的越来越快。我能感觉到他喉口的痉挛,毕竟被人操到那么深的位置会带来强烈的濒死感,他在和求生的本能对抗,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一点抗拒的迹象,反倒在努力放松下颚,任由我向前挺腰在他喉咙里抽插,努力用口腔湿热的黏膜抚慰我。可爱的乖孩子……我决定给他一点奖励,微微动了动食指,停在武器架上的贤具立刻无声地飞了过来。
他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贤具,眼珠从左向右转动,然后双眼突然睁大,身体往前耸动了一下。贤具并不光滑,末端有凸起的魔纹,幸好机工去见朋友前还在和我缠绵,他的屁股里不只有融化的润滑,还有我早上射进去的精液。被以太操控的器具不知道怜悯,撞得他整个人都在摇晃,机工发出了沉闷的声音,像尖叫,也像呻吟,全都堵在他被塞满的喉咙里。我眯眼笑着,勒紧手里的长鞭,让我和他更紧密地贴合在一起,他被我拽的跪直了些,贤具找到了好角度,自下而上狠操了进去。
我的恋人,我美丽的人偶在发抖,他的双眼开始翻白,下颚张开的角度近乎脱臼,可我依旧不满足。爱太柔软,幸福感比羽毛还要轻,我必须给他更锋利的东西,能刺痛他、伤害他,让他记住我的存在,永远不会忘记。随着以太加倍注入,另外三根贤具也漂浮到他身体附近,内里加热过的药剂开始向下滴落,一滴一滴,落在机工身上。
他颤抖的更厉害了。
药液凝固在他的皮肤上,为他的窒息和快感增加了新的调味品,我知道这种感受,学习如何治疗烫伤时我用自己做过实验,那种疼和皮肉被切开的疼不一样,更尖锐也更难以忍受,但他只是发抖,依旧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我。我注视着他,看他的胸口被浓稠的白色药剂烫的发红,连乳尖都被包裹其中,每一滴药水落下,他的身体就会跟着痉挛一下。人类的身体真奇妙,他因疼痛而产生的反应居然为我带来了更强烈的欢愉,我的思绪有些混乱,不知不觉间把皮鞭在他脖颈上绕了一圈,但在勒紧长鞭之前,我清醒了过来。
我可以赐予他疼痛,赐予他深深扎进脑浆里的玻璃碎片一样的记忆,但我不能夺走他的生命。我没资格。
机工还不知道自己在死亡的边缘打了个转,依旧乖顺地趴在我的身上,我揪住他的头发往后拽,让自己硬挺的性器从他喉咙里退出来,然后抬脚踹在他肚子上。那一夜的“检查”让我对他的状况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他非常健康,这样的殴打不会伤害他的身体,只会带来令人记忆深刻的疼痛。机工跌倒在地上,侧躺着,身体瑟缩着蜷成一团,用双手捂住自己泛起青紫的肚子,他没能蜷缩太久,贤具依旧像发情的野兽一样在他屁股里抽插,顶得他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他翻身趴在地上,四肢并用往远处爬,我跪下来抓住他的腰,把他拖回到自己身下。还没结束呢,这只是开始而已。
被过度使用的后穴红肿不堪,贤具抽离后甚至无法合拢,我能瞥见他被磨得充血的肠壁,以及被顶到深处的凝结的精液块。很神奇,在我俯身抱住他的瞬间,机工忽然安静了下来,他的脸颊贴在地毯上,向前伸出的双臂一点点缩回来,和膝盖一起撑起他的身体。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禁术还在生效,他认为我是他的恋人,所以他必须答应我提出的任何要求。
于是我凑到他耳边,用很轻的声音说道:“把腿分开。”
机工分开双腿,还往后凑了凑,把被鞭打过的肿起的臀肉贴到我身下。我抚上他的喉咙,一点点向下,用掌心的温度熨烫他的皮肤。锁骨,胸膛,小腹,然后是性器。精灵族的阴茎和他们的身材一样修长,一只手没法拢住,我干脆双手并用,把他勃起的性器从顶端到囊袋全都包裹起来,机工发出了很微弱的呻吟,开始晃动腰胯在我手心里小幅度地抽插。我喜欢他这幅失控的样子,也知道他还能做得更好。
后入的姿势顶得很深,我取代了贤具的位置,用和贤具一样粗暴的力度操他。无数次的交合让他的身体适应了异物入侵,甚至能在其中得到不小的乐趣,机工呻吟的音调越来越高,一点点浸润出仿佛哭腔的颤抖,我啄吻他红热的耳廓,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距离太近,我甚至能看清他脸颊上细小的绒毛,自然不会错过他的表情变化,机工紧皱的眉放松了,垂下的眼睑缓缓抬起,露出瞳孔微缩的眼珠,他的嘴角在逐渐上挑,扯出一抹暧昧又古怪的笑。他开始享受了。我深吸一口气,低头用鼻尖蹭他汗湿的颈窝,忽然觉得喉口涌上一阵甜腥。
我咽了咽口水,用苍白的嘴唇亲吻他。
机工不喜欢接吻,或许在他的深层意识里,这种事只能和最亲密的人做,而我不在那个范围内。他偏过头试图躲开,我揪住他的额发,咬住了他的唇。强求来的吻里有血腥味,但他的唇柔软,舌尖甘甜,我吃得心满意足,亲吻加深的同时腰胯也跟着沉下去,向他还在痉挛的后穴里操得更深。机工很用力地吸着气,顶在我手心里的性器越发硬热,看起来只需要再来一丁点刺激就能到达高潮。鞭子的末端和细绳差不多,可以暂时充当一下束精环,我把它在机工的阴茎根部系好,再打上死结,机工立刻发出了难耐的呜咽。
“不、哈啊……不要……求,你……让我……啊……”
我的恋人难耐地扭动着腰臀,努力向后迎合我的动作,哪怕被操得呼吸不畅也不愿躲开,只想让我放过他,让我赐予他酣畅淋漓的高潮,可我不想让他如愿。轻易得来的幸福不会被珍惜,他必须像我一样痛苦、煎熬,在漫长的等待后吃下好不容易得来的果实,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幸福。我柔声哄着他,扶他翻身面对我,用他发抖的双腿缠住我的腰。姿势调换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和视觉冲击,他被我撞得身体不停耸动,胸肉也跟着摇晃,身上的鞭痕随着体温升高而逐渐充血,伤口里沁出一颗颗血珠。
机工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了,满心满眼都是我,脑子里只剩下对高潮的期待;他被捆起来的阴茎已经完全涨红,铃口涌出一小股精液,大部分还堵在鼓胀的囊袋里,快感和渴望堆积在他小腹深处,让他的胸口起伏出海浪般漂亮的弧线。我看着他,用手掌抚摸他,掐他腰侧那一层软肉,把他的身体拖拽下来往自己硬得隐隐作痛的性器上按。
我们交合得很紧密,下半身完全连接在一起,甚至能享受到他肠口肉窝带来的阵阵吮吸感。欲望在控制他,又何尝不是控制了我,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同时接管了我身体的控制权,我感觉不到胸口的刺痛,感觉不到以太被过度抽离的疲惫,我满心满眼都是他,脑子里只剩下与他亲密交合时才会有的兴奋。
所以,当滚烫的血从我的唇间喷出来,落在他身上时,我们都愣住了。
高潮的余韵还在四肢百骸打转,我们的交合处浸泡在温热的体液中,很快就有更热的液体淋了上去。作为医师,我不用法术就能判断出自己此时的状况——人体内的以太是有限的,一旦透支后再强行释放法术,那就只能使用另一种力量。我的生命力在不知不觉间流逝了许多,像从指缝间滴滴答答流出去的血一样往外漏。我捂着嘴,先是咳嗽,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禁书上的法术效果很好,不难,但需要的不仅是施法人的决心,它还想要我的命。
机工很安静,他好像不太能思考,不知道此时发生了什么。他顺着自己的胸口一寸寸向下抚摸,那些血随着他手掌移动被涂抹成大片刺眼的红。他没管自己满是鲜血的身体,双眼涣散着,分开双腿,把一片狼藉的下身袒露给我。
“救……”
明明摆出这样淫靡的姿势,机工嘴里吐出的单词却和此时的氛围完全不符。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救?救谁?他还是我?
我不敢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结论如何,都只会让我更痛苦。
死亡像一只巨大的逐渐充满的气球,缓慢占据了卧室的所有空间,然后压住我。我的肺泡空了,血液从我身上的每一个孔洞流出去,我躺在床上,身体微微陷入柔软的床铺里,明明盖着厚被子,却感受不到一点温暖。除了右手。机工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他的眼泪一颗颗砸在我的手背上,很暖和。
这和经历了多少次没关系,任何正常的、有情感的人类都无法直面死亡,更别说即将死去的是他最亲爱的“恋人”。机工深深弯下腰,照顾我的这几日他消瘦了许多,脊骨把衣服顶出一处处清晰的凸起,睡衣像帐篷一样覆在他身上,随着他的啜泣不停抖动。
他还没准备好接受我的死亡。我也一样。
我忽地又想到一件事,让我衰败的身体回光返照,又散发出活力来。他会记得我,我要作为他最亲爱的“恋人”死去了。他会一刻不停地哭泣,为了我,直到他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濒临死亡,在咽下最后一气之前,他都会反复念我的名字。我握住他的手,在喉咙呛血的咳嗽声中挤出最后的遗言。
“你、要……记得……我……”
机工强行把手从我的掌心里抽走了。我看见他的手背上有很清晰的白痕,他的皮肉被我掐的暂时失血,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颜色。我看见他的脖颈和胸膛在发出微光,那是咒文。禁术失效了。
“你都做了什么?!”
他站了起来,椅子被他撞倒在地上,发出巨大刺耳的噪音。我被这一声惊醒,立刻抬头看向他。啊啊……他的目光……那是怎样充满仇恨和愤怒的目光啊……我从他最亲爱的变成了最痛恨的,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要死了……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浑身冷汗淋漓。
客厅里很昏暗,只有壁炉前的休息区点了一盏台灯,机工坐在沙发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很长。我绕过他的影子,坐在他对面的位置。
平时放着茶点饮品的茶几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有枪,不仅是枪,还有一条金属制成的类人形的手臂,机工正在用螺丝刀拧开它。他很认真,直到我的身体和沙发挤压出咯吱声才发现我。“你看起来很累,不再休息一会儿吗?”机工笑着问道,仿佛几星时前我对他的暴行只是一场梦,他的笑容依旧温柔,双眸里满是对我的担忧和……爱。
那份爱的来源是我刻在他身体里的咒文。我忽然觉得好滑稽,笑声脱口而出,变成了一句疑问。
“你在做什么呢?”我问他。
其实我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一周多的时间里,他除了照顾我和陪我做爱,大部分空闲时间都在做这些事。这些东西是他的得意之作,他每天都要护理一遍,逐个擦拭上油。
“这是后式自走人偶的手臂,我对它做了一些改装,可以释放威力更大的技能……”
机工用螺丝刀当做教鞭,指着机械手臂侃侃而谈。我盯着那些金属和复杂的线路,仿佛在它们之间的缝隙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只属于他的世界,他只有在那里才能熠熠生辉。如果不是我的出现,此时的他应该还在天钢机工房,将自己的知识慷慨地分享给所有人,包括但不限于那些欣赏且爱护他的同僚,可我为他拴上了铁链条,把他拽到自己身边,关在了名为爱的笼子里。
我到底是爱他,还是爱他曾经给予过我的温暖?
“只要调整这个零件,就能控制自走人偶施加在手臂上的动力……”
“过来。”
机工还在说他的研究,我打断了他,对他招手。他微微愣了一下,但就马上起身走到我面前,跪在了地毯上。
壁炉里火光摇晃,他的脸浸在昏黄的光线中,我仔细看他的眉眼,又用手摸了一遍,始终找不到记忆中那个少年的痕迹。我笑了笑,将他拥入怀中,在他背上一下一下地轻拍。
“祝你幸福。”
咒文缓缓亮起,被强行撕碎的禁术化作以太消散在空气中。我把他抱紧了些。
“祝你健康。”
禁术消散,反噬紧随而来,我咳出一口血,用手背擦了擦嘴。他有些疑惑,微微用力挣动,我按住了他试图抬起的手臂。
“祝你一切都好。”
即将枯萎的植物可以挤出汁液,濒临死亡的躯体也能榨出以太。我把最后一点以太凝结在指尖,轻轻点在机工脸侧,为他施加催眠法术。他身子一抖,忽然从喉咙里挤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仿佛大梦初醒,又仿佛陷入了另一个梦里。
“走吧,你该回去了。”我捂住他的眼睛,推他转身,站起来,然后往玄关走,“外面下雪了,记得穿我的大衣,深灰色那件,皮毛的,暖和。”
机工走得很慢,我能感觉到他睫毛的颤抖,扫过我的掌心,留下最后一点柔软的触感。我推着他走到门口,最后看了一眼他的背影。他弓了一个多星期的腰不知何时挺直了。
“走吧。”
我推了他一下。他扯下挂架上的大衣,没有任何迟疑,冲进了外面的风雪里。门还开着,风卷着雪花打在我身上,我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不是风雪带来的,是从我的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
门很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它关好,然后又用了许多时间慢慢挪回到壁炉前,拿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柔软的沙发逐渐变得坚硬,柴火还在燃烧,却没有散发出温度。我瑟缩着蜷起身体,忽然感觉到有人坐在了我旁边。
“你看起来很累,不再休息一会儿吗?”
少年调整了下姿势,侧身把肩膀送到我面前。他很瘦,脸颊因为营养不良而凹陷下去,双眼却亮晶晶的,盛满对所有人的温柔和爱。我把头靠在他肩上。他好瘦啊,肩膀硬得木地板,还很冰冷。我把毯子分给他一半,搂着他的腰闭上了眼睛。
我爱你,我的朋友……
–
大雪之后是难得的晴天。
机工赖床了一小时才慢吞吞地爬起来,他觉得好累,就仿佛穹顶皓天是他昨夜一个人建起来的似的,幸好伊修加德人早就习惯了这份寒冷,离开温暖的被窝后,冰冷的空气和水龙头里流出的冷水都能让他迅速清醒过来,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工作。
“对了,今天要做什么……”
机工小声嘀咕着,穿好皮大衣出了门。对面的房门正好也打开了,一位天钢机工房的职工走出来,看见机工后惊讶地“咦”了一声。
“你回来啦!”男人热情地向机工打招呼,“好久不见了,你休息的怎么样啊?”
休息?
机工愣了一下,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对,休息。他请了一周的假,说是要好好休息一下,顺便照顾一位……
……
……
……
谁?
“我休息的很好!已经随时可以投入工作了!”
机工咧嘴一笑,举起手臂,做了个展示肱二头肌的动作。
“那就好!上次见到你我还有点担心来着,你那位朋友气势可真足啊,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敌意呢……”
对面的男人也露出笑容,伸手揽住机工的肩膀,搂着他往外走。机工听得不明所以,有心想问,话到嘴边却没说出口。
朋友?
不记得了,应该不是很重要的人,还是考虑今天的工作比较重要。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